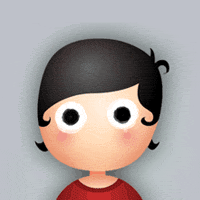白玉镯(下) 文/吴沉水
请输入标题 bcdef
【 白玉镯(下) 】
文/吴沉水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刘士季办完这件案子,也需离开建昌县,转去南康道其他地区巡视了。临走那日,许璋自是送别到城外,却不料送没多远,就被刘士季轰走。
理由是我又不是不回来,你建昌县又有大案,自然还需请示本提刑。
五
建昌县仵作乃老少二人,老的是师傅,人称鬼脸张,好端端一张脸,半边全是青痣,“鬼脸”一名由此得来。他于仵作这行一做便做了二十余年,独来独往,无亲无故。不知何时,其身后多随了个孩子,左腿微瘸,称他做师傅,建昌县百姓便晓得这是要承鬼脸张衣钵的小徒儿,徒儿也姓张,人称瘸儿张。
师徒二人进了公堂,先给刘士季许璋叩头行礼,刘士季道请起,问:“张师傅,且将田文锦致死缘由于这公堂上说上一说。”
“是,”鬼脸张道,“田文锦身上刀口共一处,位于左侧肋下三寸,宽一寸二分,皮肉不平整,深扎肾部。此处乃人体要害,下刀后不出半盏茶功夫便会毙命。依小的看,杀人者若不是撞大运碰了巧,便是行家里手。”
刘士季笑了笑,道:“可现下有两名女子争抢着认人是自己杀的。”
鬼脸张老于世故,晓得验尸后的事不归自己管,便笑笑不作声。可他徒儿却正值年轻气盛,一听便冲口而出道:“女子?那得多大力气的女子啊?一刀扎入肾部,这气力好比持刀一下刺透千层纸,女子若非天生神力,便得是自幼练武或做活之人。”
刘士季温和地道:“可有位闺阁女子,信誓旦旦称人为她所杀。”
“那,难不成她杀人的匕首是吹发能断的神兵利器,不然怎么能够?”瘸儿张一句话没说完,脑袋上已经被他师傅打了一下,鬼脸张骂道:“臭小子,此乃公堂之上,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敢于对着提刑大人胡扯八道!还不跪下请大人赔罪?!”
瘸儿张摸着头不敢回嘴,正要下跪,刘士季笑道:“小张师傅快莫如此,本官还待请教几句,若要跪,这下面的话便不好问了。”
“提刑大人,您让我们站着回话,已是给了天大的恩典,小的却不该忘了本分。”
刘士季问:“张师傅,以你所见,凶手可能是闺阁女子,面对面将刀刺入田文锦体内?”
鬼脸张想了想道:“不能。田文锦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女子若不是练家子,持刀不该能近其身。且刀口倾斜朝下,证明持刀者乃手握匕首用力往下扎,寻常女子定然较之田文锦矮,面对面持刀,刀口该朝上才对。”
刘士季赞许地点点头,转头瞥了眼已经呆在当地的张妈与季氏,问:“那若仆妇持刀,有无可能?”
鬼脸张点头道:“不在常理之内之人事皆会存在,仆妇气力较之闺阁娘子自是大了许多,只是……”
“如何?”
“那伤口不平整,非一刀所致,倒像有路过的瞧不过眼,在同一位置又补了一下。”鬼脸张迟疑着道,“亦有可能是刀入体内,持刀者恨意难消,照着刀口又补多一刀。”
“张氏,”刘士季重重一拍惊堂木,喝道:“你言道当日于皆有混乱中心怀杀意,于是持刀杀死田文锦,那是一刀还是两刀?”
张妈嘴里塞的布条被取走,她煞白了脸,结结巴巴道:“两,两刀。”
“怎的你上回供词却称刺了一刀?”
“老奴,老奴记错……”
“荒唐!”刘士季怒道,“人命关天,岂容你儿戏!你到底刺了几刀?”
“两刀,是老奴所为,老奴刺了两刀。”
“那为何季氏却作证田文锦乃你家娘子所杀?”
张妈大声道:“她撒谎!季氏蛇蝎心肠,却偏惯作好人,她哄骗老爷,时时插手府中中馈之事,她骗不过娘子,便怀恨在心,谎称听见老奴与娘子对谈,大人啊,娘子与老奴自幼亲厚,私下时老奴唤她可不是什么娘子,而是直呼其乳名。季氏一上来便扯谎啊大人……”
“奴,奴是,奴是怕娘子乳名不可在外直呼……”
“那你说,娘子的乳名叫什么?”张妈厉声问,“你一个八十贯便可买卖的妾,如何知晓娘子的乳名?”
季氏哑口无言。
刘士季却道:“季氏扯谎,你却也不曾说实话。张氏,彼时情况混乱,田文锦一丝尚存,你便是心怀恨意连刺两刀,又如何能准确刺入同一处刀口?”
张妈顿时闭上嘴。
“本官一直有一处不明,还望季氏与本官解惑。”刘士季缓缓问,“你为田家妾,只侍奉田县丞,与田娘子却无瓜葛,且听适才张氏所言,你不仅与她无瓜葛,还时不时有些矛盾,田娘子多年在室,想必也令你颇为嫌恶,这样的状况下,你如何说服她出来顶罪?”
“人皆有欲,不为名,便是为利,不为利,便是为义,不为义,也能为忠,不为忠,便能为孝。”刘士季盯着季氏,直到她瑟瑟发抖,才慢慢道,“田娘子与你,唯一联系便是田县丞,田县丞乃其父,那么,田娘子是为孝。”
“你是如何用孝打动她?”
刘士季轻轻吐出一口气,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季氏,你给了田县丞什么能说服田娘子拿命来换?”
他盯着季氏,一字一句问:“想来想去,你手中最有力的牌也不过是子嗣香火一流。对了,田县丞那个妾生子叫什么?田文宇?”
季氏身子一软,歪到一旁,她呆了呆,忽而爬起,重重磕头道:“大人,奴招了,奴全招了,田文锦乃奴所杀,不关二爷的事,一切皆是奴贪心不足,是奴不守本分!是奴自作聪明!”
刘士季掉转视线,冷冷道:“你道公堂如田府私宅,由得你翻手云覆手雨?无知愚妇。来人,传田文宇。”
季氏一听田文宇三个字,霎时面如死灰,瘫倒在地。
六
蔓草凄凄,一望无际。
刘士季带着王德忠骑马而行,后面随着两名僮仆。
“大人,后头那辆马车已随了咱们一路了。”王德忠悄声对刘士季道。
刘士季头也不回,道:“且由它去。”
王德忠忍不住再道:“可……”
刘士季淡淡地问:“怎的,担心车内的女流之辈行刺本官时,你收拾不了?”
王德忠笑呵呵道:“怎会呢,大人说笑了。”
刘士季马鞭一摔,策马狂奔,王德忠吓了一跳,赶紧乖乖纵马跟上,再不敢多言语一句。
今日乃刘士季生母冥诞,往昔几年刘士季在外为官,忙忙碌碌,此番巡视南康道,又亲临建昌县,这一日自然要来母亲墓前祭奠一番。
他自为官以来,每年遣人返乡为父母坟头加固洒扫,整修墓园,许璋任建昌县县令以来,更是多方照拂刘氏坟冢,故现下刘士季父母的墓地较之落魄当年,已不知光鲜整洁了多少。刘士季下得马来,早有僮仆上前布好祭奠果品香烛,刘士季照着规矩行礼叩首,又焚了一篇亲笔祭文,以慰父母在天之灵。礼毕,他伫立良久,脑子里不知怎的,忽而想起母亲当年含笑打趣他的话:“若不好生读书,来日叫新妇腹诽取笑,母亲可是不管的。”
音容笑貌宛如眼前,可慈母长逝,那记忆中明亮耀目的少女,却也湮没到无处可寻。
刘士季默默闭上眼,耳边风声猎猎。
良久,他睁开双目,对王德忠道:“你去问请那马车上的人来此。”
王德忠一愣,随即道:“是。”
他去了一会,便带着一老妪并戴着帷帽的娘子前来,正是已无罪释放的田娘子与张氏二人。
当日公堂之上,季氏虽欲将杀田文锦之罪揽到自己身上,然田文宇却亲口承认,田文锦乃他所杀,田乐婉此前顶罪,不过为护住父亲一脉子嗣,而他被季氏锁在家中不得外出,有口难辨,无法亲临公堂自首。他虽是少年,然生得手长脚长,平素爱舞刀弄枪,力气不小,且那匕首乃他之物,田乐婉闺阁女子,怎会有利器在身?刘士季甚为干脆,当即便将田文宇收监候判,季氏以妾诬告嫡女,乃以下犯上,一并押下不提。
案情至此已算大白,便差判词一写,落下帷幕了。
可田娘子却找上门来,几次三番被拒后,甚至尾随刘士季至刘氏墓地,这般胆大妄为,刘士季已不知该怒抑或该以冒犯朝廷命官为由将她再抓起来算了。
然转念一想,母亲生前极是满意为他聘田氏女为妻,或者瞧在母亲面子上,见一见也无妨。
田娘子一走近,便朝他行了礼,双膝一屈,又欲给他父母叩首。
“且慢。”刘士季冷冷道,“你已非刘家妇,此礼家父家母受不得。”
田氏女却清脆答道:“妾如今确非刘家妇,不得为二老披麻戴孝。然刘老爷生前疏财乐施,曾救困厄无数,遇荒年捐资数以万计。刘夫人经理内治,虽于富贵之家,却勤俭自力,衣粗食粝以资夫君善行,从无怨言。二老高风亮节,妾心向往之,受大礼亦不为过。”
她说罢也不理会刘士季,上前恭恭敬敬对着墓碑行了大礼。刘士季有些无奈,却也不好真个阻拦,待她礼毕,禁不住冷声道:“田娘子,今日本官见你,乃看在先母份上,你莫以为磕几个头,说几句好话,便能为你弟弟开脱,扰乱断案清明,本官一样可拿你……”
田氏女侃侃而谈道:“妾怎敢有次妄想,妾此番前来拜见大人,却是信大人乃中正君子,清廉无私,绝不姑息奸恶,亦不会冤枉好人,故来与大人指出些案情疑点,绝非有意为舍弟开脱。”
“倒是牙尖嘴利。”刘士季看着她蒙在帷帽之下朦胧的脸庞,忽而叹了口气,他道:“田娘子,你与田文宇感情甚笃,关心则乱,也是人之常情。然生死关头却最是作伪不得。你之前若非确信田文宇便是凶手,又何必舍不得他死,毅然要出来替他顶罪?现如今你再多说什么,只显得欲盖弥彰,又有何用?”
田娘子毅然跪下道:”当日情急之下,若妾不认了这个罪名,二叔定不肯善罢甘休。而弟弟问罪,家中再无男丁,二叔轻易便能置妾于死地。可若妾顶罪,则弟弟得保,妾已使巨资令族内各宗亲松口,同意弟弟记在先母名下,由妾生子变为嫡子,届时大房资财并先母遗下的嫁妆,皆由弟弟继承,无人再能有异议。大人,现下舍弟被收监候斩,族内群狼虎视眈眈,妾已是朝不保夕之人,求大人容妾禀报实情,说完后若仍信舍弟乃凶手,妾亦无怨言。”
刘士季不语,却负手而立,过了一会,他有些感慨,轻声道:“你这般聪明,定然想到了,刘怀安若非念及旧情,便不会救你出狱。只是田娘子,今日在刘某先父母墓前,你若真个感念二老仁厚,便须知适可而止远比得寸进尺更好!”
这话说得太重,田娘子身形晃动,却强撑着,一字一句道:“求大人,请听完妾一席话。”
刘士季转过头,眼神清冷,道:“起来吧,讲。”
田娘子爬起来,一个踉跄摇摇欲坠,张氏欲上前扶她,却被她摆手示意不用。她深吸一口气,道:“此事须得从头说起,先母早逝,其嫁妆全部遗与妾。父亲膝下只妾一个独女,自幼爱若珍宝,常恐妾出嫁后为钱财所困,故亲寻可靠人等经营妾之嫁妆,不出十年,已有百万之巨。当年,先父闻刘家颓败,大人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他老人家生怕妾受委屈,更怕大人冲妾的嫁妆而来,非真心良人,故执意退亲。”
“这些本官早已知晓。”
“是,”田娘子低头道,“先母去后,先父无人照料,二叔田通仕便出了主意,让父亲租妾。季氏先几年倒安分守己,生了弟弟后却越发目中无人。妾把持府内中馈,不肯令其沾染钱银,她便常年兴风作浪,搅得家中不得安生。天可怜见,她生的弟弟,却是自小极得人疼的。家中无主母,妾便以长姊为母,亲教其读书写字,他好动,妾便寻武师傅教习棍棒,磨他的性子。弟弟生性忠厚兼良,与妾倒比与季氏亲近。妾原已打定主意一生不嫁,有弟弟为靠,也是心安。”
刘士季听到此处,禁不住看了她一眼,只隔着帷帽,却不知她脸色神情如何。
”大人,舍弟与田文锦交恶,固然是二叔父子贪婪大房财物,然究其根底,却是因妾而起。先父去世后,田文锦行事越发狂肆,没了顾忌,数次见妾,目光均不怀好意。妾深恐遭他下作手段暗算,便雇人,雇人尾随打探……”
刘士季忍不住训道:“你一个闺阁女子,怎会晓得这些市井手段?没规矩!”
田娘子反唇相讥道:“妾无母却有财,犹如七岁稚童身怀和氏璧,若一味遵规蹈矩,又如何自保?如何端正门风,教导幼弟?”
刘士季不知为何生不了气,反倒生出几分怜悯,他叹息道:“继续。”
“妾所托之人乃舍弟武师傅同门,也算此行好手。不出三日便带了消息来,却原来妾那同宗兄长欲寻匪类将我劫走,想远远卖与人做妾,再谎称妾遇害身亡,自己过继入嗣,便能霸占家产。”
刘士季心里微微一震,瞧向田娘子。
田娘子却平静地道:“妾未及笄便已常应对二叔一家这等层出不穷的龌龊事,心中早料得田文锦有朝一日定会丧心病狂谋财害命,故闻此言并不甚吃惊。可舍弟不过成童年纪,性子难免急躁,他自幼由妾教导长大,怎能忍这些事?过不了半月,舍弟便慌里慌张跑来与妾说,他杀了田文锦。随后季氏尾随而来,又是叩首又是哭喊,妾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再将其间厉害关系想明白,便当机立断,命季氏拖住舍弟,自己带了张妈上衙门认罪。”
刘士季沉吟片刻,问道:“田文宇是否与你说,那夜见天色暗黑,田文锦不知自何处吃醉了酒满嘴胡沁,你弟弟与之理论,却被其推搡,于是一怒之下拔刀相向,失手将其捅死?”
“是,”田娘子抬起头,恳切地道,“可是大人,当夜吃醉酒的,不是田文锦,而是舍弟啊。”
刘士季眼睛一眯,想了想,忽而道:“只怕此间关键,还需着落在季氏身上。”
田娘子大喜,立即跪下恭敬磕头道:“大人且放心,妾与那季氏交锋十余年,早已将此女秉性了如指掌,大人大恩大德,田氏肝脑涂地无以为报。”
刘士季莫名其妙心软了,他亲自弯腰扶起她道:“起来吧。”
七
初五正日,刘士季整顿官服,瞥了眼一旁侍立的王德忠,问:“如何?”
王德忠笑嘻嘻道:“大人自然是雄姿英发,官威十足。”
“不好读书便是如你这般,连句奉承话都说不利索。”
“小的嘴皮子不利索,心意至诚就是了。”王德忠笑道,“今日断案下判词,外头可来了好些建昌县的百姓。”
刘士季点点头,不置可否。
王德忠想了想,低声道:“田娘子带着张氏也来了。”
“田通仕呢?”
“也来了。”
刘士季道:“许大人爱民如子,此刻必与百姓父老寒暄,咱们不忙打扰,我且问你,昨日田娘子可去了女牢?”
“去了,她进去后与季氏谈了一盏茶功夫便走。”
“这么快?”刘士季皱眉问,“牢头不曾听得只言片语?”
王德忠小心地瞥了他一眼,道:“只听得田娘子道,我田乐婉为庶弟且敢舍百万家财,身家性命,你身为人母,却只能享福不能共难不成?”
刘士季微微一笑道:“这娘子忒得一张利嘴。”
王德忠疑惑道:“三言两语便能令人以身赴死,这娘子怎的比男儿更果敢坚毅?”
刘士季不知为何不耐起来,喝道:“女子当以贤淑温顺为本,她这是没规没矩,哪当得起果敢坚毅四字?”
王德忠忙赔笑道:“大人说的是,若小的家中婆娘如此有主意,小的早一巴掌呼下了。”
刘士季却被“家中婆娘”四字微微动了心,他愣怔片刻,随即回复清明道:“啰嗦个甚,走吧。”
“是。”
公堂上果如刘士季所料那般热热闹闹,许璋为官亲和热忱,深得此地百姓喜爱。刘士季进去时,只见许璋被人团团围住,这个道许大人家中有弄璋之喜想请您去吃个酒;那个道许大人园子里春桃盛开煞是美景,许大人哪日挪步观赏则个。许璋笑呵呵地一团和气,瞧着甚为愉悦。
今日宛若不是断人生死的判案日,倒像开坊市般喧哗。
刘士季清咳一声,王德忠唱道:“刘大人到。”
众人皆静了下来,许璋面带微笑迎上去,两人先见了一番礼,这才谦让着坐下。刘士季一拍惊堂木,道:“传人犯田文宇,季氏。”
田文宇今年不过十五,却长得孔武有力,眉目间与田乐婉不甚相似,只一双眼同样清澈澄明。他跪下后脊背挺立,这点亦与田乐婉相同。刘士季看着跪着的少年,问:“田文宇,田文锦可是你所杀?”
“是小的所为。”
“你为何杀他?”
田文宇振振有词道:“田文锦人面兽心,妄图贪我大房家财。家姊有嫁妆百万,他便心生毒计,与匪类勾结,商议趁我家姊出门上香之日将之劫下,远远发卖与人做妾,再谎称其已毙命,入嗣我大房,便能独吞资财。长姊如母,小的便是粉身碎骨亦不能令长姊受此欺侮。小的不后悔宰了他,小的只恨被生母锁入宅内,累得家姊前来顶罪受了委屈。”
他长相端正,声音洪亮,这番话一出,堂下众人纷纷议论,皆道虽杀人行凶,却也是情非得已。
刘士季问:“你不过一成童年纪的儿郎,又如何得知田文锦的毒计?”
田文宇有些茫然,道:“自然是听人说。”
“谁?”
田文宇困惑地道:“是小的听得生母季氏与丫鬟窃窃私语。”
刘士季又问:“你虽习武,听闻平素家中管束甚严,连架亦少打,平素也不是惹是生非之泼皮无赖,杀人这般大事,你如何下得了手?”
田文宇立即道:“心中恨极。”
刘士季点头道:“却原来你往日不恨,只听得田文锦要卖你家姊为妾才恨。是与不是?”
田文宇面露愧意,垂头道:“往日也是恨的,那夜恨意最浓。却不是,却不是为卖我家姊……”
“哦?”刘士季又问,“田文锦还做了何事?”
田文宇满脸通红,道:“大人恕罪,小的,小的宁死不说。”
刘士季淡淡道:“你不说亦要死,只可惜你家姊教导你的一番苦心,亦可惜了她甘愿为你顶罪的果敢坚毅。”
他顺势便用了“果敢坚毅”一词,说出口才意识自己失言,转头瞪了王德忠一眼,王德忠待笑不敢笑,忙低下头装看不见。
刘士季清咳一声,道:“田文宇,本官再问你,田文锦又做了何事令你非杀他不可?”
田文宇眼中涌上泪雾,却倔强地一言不发。
“大人莫要为难他,”季氏慢条斯理地道,“奴替二爷答话便是。”
“二娘。”
“二爷,是奴对不住你。”季氏抬头,目露眷恋,柔声道,“奴身份低微,见识浅薄,生下你养到启蒙,老爷便决定将你交予娘子教养。奴初时亦是不依的,然老爷道难不成让孩子跟着奴,长大后习歌舞唱曲?奴这才狠狠心答应了。二爷,你可记得,你年幼之时离开奴,哭得有多凄惨?”
田文宇哑然道:“记得的。”
“幸得娘子待你全无私心,她将你教得忠厚仁义,顶天立地,可奴心里苦啊,每次瞧见你与她亲厚,奴心中宛若刀割一般,二爷,你常劝奴莫无事生非,然若不时时寻些事端,二爷又怎会记得奴才是生你那个人?”
刘士季冷声道:“季氏,本官今日可不是来听你叙旧。”
季氏擦擦眼泪,道:“是,大人。二爷会恨田文锦至深,除了田文锦欲卖了娘子外,还因田文锦数度酒醉后欺侮奴所致。这等话,二爷一个未成年的儿郎,自是说不出口的。”
她一言既出,堂下哗然一片,季氏面无表情,继续道:“可将田文锦所做种种恶事传入二爷耳中,却是奴有意为之。”
“二娘,你是想我替你报仇,我晓得。”田文宇道,“我不悔,杀了他我不悔。”
季氏摇头道:“奴并非要二爷报仇,奴只是要二爷杀了田文锦,可最终杀田文锦的,却不是二爷,而是奴。”
田文宇大惊,道:“二娘你胡扯什么?我杀的人我怎会不知?那夜田文锦吃醉酒踉跄而行,我,我上前去拿着匕首刺了他一下,我分明记得的……”
“二爷,你那夜也吃了酒,你忘了么?武师傅相邀,你出去作陪。奴恐你吃多酒会身子不适,特命丫鬟等在二门上。你一踏入巷子,奴便晓得了。奴怕你醉酒,赶着过去相扶,怎料一去却见你醉倒地上,手持匕首,而那田文锦已中刀倒地,血流不止。”季氏面色平板无波,宛若讲旁人之事一般淡淡地道,“奴去的那会,田文锦尚未气绝身亡,他还会爬,奴等了这许久,天大的机会终于在眼前,又怎肯让他爬走求救?于是,奴拿了二爷的匕首,照着他腰上的伤口,再刺了进去。”
刘士季点头道:“怪不得张仵作道,刀口不平,似是有人连刺两下。”
季氏道:“田文锦一死,奴便哭到娘子跟前寻死觅活,又故意走漏田文锦被杀的风声,令娘子无毁尸灭迹的回旋之地。她那般聪明之人,只因牵涉到二爷,却也乱了心,不用奴多说,她亦懂得此中利害,于是她便命奴将二爷看起来哪也不许去,自己痛定思痛,决意去顶罪。奴数年谋划一朝得成,一下除掉两个心腹大患,那几日欢喜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可惜了。你们一群妇孺,皆以为本提刑是好糊弄之人,错漏百出的证词,也敢拿来本官跟前现眼。”刘士季冷冷地道,“季氏,你今日便是不坦白,本官亦已派人将你的丫鬟扣起,并在你房中搜出与田文锦私通的罪证。你明明乃通奸,却要诓骗亲生儿子是被强迫,你明明已有一千贯私房,却偏生贪心不足,却非要谋原配陪嫁,是谓不安其分,罪有应得,本官判你锄邢,你可心服?”
季氏面如土色,抬起眼,颤巍巍地道:“奴尚有一言对二爷说,望大人准许。”
刘士季不加阻拦,只见季氏泪流满面,对田文宇道:“二爷,奴给不了你什么,便想为你谋多些家产,奴皆是为了你好,你莫要恨奴,可好?”
田文宇面露痛楚,仓惶地转头不看她。
季氏无法,只得伏身痛哭。
八
季氏按律当斩,田文宇却是为生母与家姊出刀伤人,其情可悯,折成臀仗四十,这般打下来,便是田文宇身强力壮,也先去了半条命。
田通仕教子不严,纵子行恶,夺了通仕郎衔,且他强要田文锦入嗣亦被驳回,田娘子早已上下打点好,只待田文宇养好伤,便可拜祭祖宗,禀明族内,将之记在田县丞先夫人名下为嫡子。
刘士季办完这件案子,也需离开建昌县,转去南康道其他地区巡视了。
临走那日,许璋自是送别到城外,却不料送没多远,就被刘士季轰走。
理由是我又不是不回来,你建昌县又有大案,自然还需请示本提刑。
许璋笑了笑,瞥见原处一辆马车静候多时,心下了然,便也不多说,与刘士季拱手作别。
待他走远了,刘士季方才命王德忠带着僮仆候着,他自己纵马上前,跑在那马车前头,隔着帘子张嘴训道:“田娘子,你又这般抛头露面,成何体统?你幼时习的女戒规矩呢?都还与令尊令堂了么?”
田娘子在里头答:“妾与大人隔帘相望,算不得抛头露面,大人少忧些不相干的。大人与妾有大恩,今日将辞,妾怎可不来作别?”
刘士季忽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舍,他清清嗓子道:“你,往后有何打算?”
“妾当紧闭门户,主持家中生计,管教幼弟,日后待他娶新妇后,便将家计交与新妇。”
“这倒是应当。”刘士季言不由衷说了句,随后又禁不住问,“难不成,你便不为自己打算?”
车内之人良久无语,就在刘士季颇以为此话唐突之时,田乐婉忽而道:“大人,其实,妾之前乃是见过大人一面的。”
刘士季诧异道:“何时的事?”
“十年前,父亲强退了亲,妾死活不依,好女子岂有配二夫之理?妾后来听闻大人为族人驱赶,贫病交加,流落在驿站。妾心中焦急,便,便不顾颜面,包了些金银首饰,托张妈交付驿站主使,命他与大人煎药延医。”
刘士季心中震动,脱口而出道:“我怎的不知?”
“大人那时病得人事不省,又怎会知?妾彼时尚年幼,大胆莽撞,便趁着张妈与驿站主使交涉之时,偷偷下车自窗外瞧了大人一眼。”
刘士季脑中一片空白,问:“你,你为何不说?”
田娘子带笑道:“妾与大人自幼定亲,拿金银资助大人本是应当,有何可说?后大人显贵,妾与大人再见竟在公堂,又有何颜面提这些?如今事过境迁,大人定已有妻妾,妾亦有幼弟仰仗,这些陈年旧事,说说便无妨了。”
刘士季喃喃地道:“我并无妻妾。”
“大人说甚?”
“我自与你退亲后,觉天下女子皆苟且无情,并无娶妻,更无纳妾。”刘士季深吸一口气,坦然道,“与你重逢后,方知自己狭隘。田娘子,娶你为妻,乃先母所定,却也是我少年所愿,怎奈造化弄人,兜兜转转,却走到今日这般境况……”
他忽而一笑,道:“今日这般境况,又焉知不是另一番机缘?田娘子,伸出手来。”
“大人……”
“把手伸出来,我不训你不知礼。”
田娘子迟疑了半日,终究轻轻聊开马车帘子,自内伸出手来。
她手腕白如霜雪,十指纤长柔美。
刘士季下了马,自怀内将那玉镯掏出,放到她手掌上,道:“这回可得戴好了。”
田娘子一惊,险些将玉镯摔下。刘士季眼明手快握住她的手,接住玉镯。
田娘子颤声道:“大大人……”
刘士季将手镯给她戴上,笑道:“不许拿下,便是穷到没饭吃,也不许拿去换,回来我要查。”
田娘子半响才低声道:“刘怀安,你可想好了?”
刘士季长长吐出一口气,道:“是。”
他翻身上马,回头看了一眼,道:“等我。”
随后不待回应,便纵马离去。
他身后的车子越来越小,小到再也瞧不见,可他心里却觉得越来越满,满到有什么东西可以溢出来。
王德忠见他踌躇满志,却有些说不出的忧虑,上前低声道:“大人,您已决意娶田氏女么?”
“怎的,你有意见?”刘士季回头斜觑他一眼。
“不敢,只是小的忧心,若日后田氏女晓得那田文锦,其实乃死于大人之命,她一家险些因此遭了祸端,不知会作何想……”
“多虑。”刘士季冷漠地答,“田文锦父子当年骗我父吃官司,累他老人家病逝狱中,我一直忍着没动他,是为公法不寻私仇。谁知他自己冲撞到我跟前妄图行贿,要我判他入嗣合法。当真痴心妄想,你说,不杀他怎消我心头之恨?也是你出刀功夫浅,一刀下去,人竟然没死透,倒惹出这么些事来。”
王德忠道:“小的那是被突然出来的田文宇惊到,未免给人认出,这才匆忙离去。”
刘士季淡淡地道:“田氏女日后是要做我夫人的,未免我夫妻生隙,这事你就烂在肚子里吧。”
“是,大人。”
(完)
请输入标题 bcdef
借
我相爱一场
好
把悲哀排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