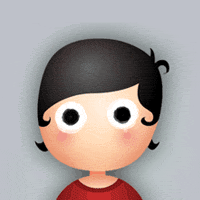徐策《上海霓虹三部曲》的第二部《魔都》
疾风暴雨中的人性光芒或缺陷,《魔都》续写《上海霓虹》
文汇出版社 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徐策,上海人。上海广播电视台一级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先后任《上海电视》《每周广播电视》等报刊执行副主编、主编。1980年代发表过《冬夜》《有四棵树的秋景》《离婚》《9平方》等中短篇小说。
《魔都》是徐策长篇小说《上海霓虹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上海霓虹》已于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魔都》以苏州河边曾有“亚洲第一公寓”之称的“河滨大楼”为叙述场景,以“新上海人”娇鹂、祖鸿的“叔嫂恋”为叙述主脉络,勾连起席秉逊一家、席秉逊的女婿及其亲家一家、娇鹂亡夫的婚外情女子单苏和隐瞒了的私生女妹妹头、“围棋国手”缪镜吾一家等等。这些寓居在曾是华洋杂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公寓里的新老移民们,构成了一道颇具上海情味的文化风景线。尤其在1960年代纷纭繁复的历史变动中,河滨大厦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曾经显赫一时的,还是始终挣扎在底层的,都被卷入其中。但在历史的喧嚣里,仍残存了个体生命细弱却坚韧的喘息。诚如沈嘉禄所言:“《魔都》重返历史现场,注重肌理感,细节的保鲜度,不可复制性,超越个人遭遇的苦难与迷惘,以史诗的眼光看待史诗……”写的是一栋楼里的人情冷暖,亦是一段厚重的历史。
《魔都》提供了阅读上海的一种视角,人物对白是沪语,有续写海派文学的野心;同时,徐策又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常有大段的内心描写,迂回往复,将“叔接嫂”等事件下人物的心理写得淋漓尽致。两者结合,让《魔都》呈现出特异的面貌,为海派文学增添了不可或缺的质素。
(甫跃辉)
序
◎ 袁念琪
《魔都》是徐策的新作,为他2011年出版的《上海霓虹》之续篇。小说继续讲述苏州河边那栋上海著名公寓——北苏州路400号河滨大楼里的故事,人物在发展,情节在推进,所处的年代也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进了60年代。
小说的主角娇鹂和祖鸿是进入都市的移民,他们来自浙江绍兴;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新上海人”。这两个乡下人先后到上海,都在祖鸿哥哥祖堃1948年到沪稍后的日子里。若要以移民论代,他们这一拨可算是民国时期移民上海的最后一代了。
上海是座移民的城市,梳理历史,迁移上海的高潮可上溯到12世纪的北宋靖康之乱,近代则在晚清上海开埠后的太平天国时期,、旋而是太平军进军苏锡常、小刀会风起云涌;掀起一个移民高潮。
当代的移民高潮,则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八·一三”为甚;还有中原江淮等地的天灾。此外,移民上海的另一要素是人口城市化趋势所致。据解放后1950年的调查,客籍人已占全市人口的85%。到21世纪的2001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外来人口为387.11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3.13%。
移民对上海的繁荣和发展的贡献,那是不言而喻的。在当下的文学作品里,表现移民上海中的成功人物不乏,而以描绘其中的普通人却是鲜有。徐策的《上海霓虹》第一部《上海霓虹》和第二部《魔都》,以新的视角、新的开掘和新的实践拾遗补阙,丰富了上海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并计划继续以“亚洲第一公寓”河滨大楼为中心舞台,以多卷式长篇小说来展现普通移民的上海生活;实在是令人期待。
祖鸿和娇鹂的叔嫂之恋,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兄故而弟恋嫂娶嫂,古而有之;新鲜的是在不同的年代,受政经风云的影响而有不一样、甚至是出现异乎寻常的表现。
俩人从约会西郊公园、烧香虹庙的点滴袒露,到娇鹂第一次走进祖鸿屋子,祖鸿终于说出心底憋了许久的话。进而一起做缝纫贴补生活,养育四个孩子。直至祖鸿一封敞开心扉的书信,彻底消除了娇鹂强弩之末的坚守。
眼看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却被东窗事发打断:祖鸿与舅舅及旧恋人景萱合伙,欲从银行取出舅舅席秉逊这个资本家被冻存款,败露后是仨人同台挨斗于“反抽盗团伙批斗会”。这一幕令娇鹂“心里特别郁闷,胸口憋得慌,嗓子渴,眼冒金星。突然,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同时,这“眼前一黑”也把叔嫂恋的悬念存入徐策的下一部。
叔嫂恋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但落脚在结构中,并不是一串到底。全书30章,但从第8章到第10章这三章里,祖鸿和娇鹂只字未提,直到第11章再浮出水面。宛如一“十字形”建筑,从底层建造到7楼后,暂停向上,而是横过来造了3层平台。
在这3章里,乃是革命风雷激荡下的河滨大楼众生相——祖鸿舅舅席秉逊与窦婉芷、围棋称雄的缪镜吾、三代白相电影机的项炳其与夏慧莹、原黄金大戏院头牌花旦佟颖倩和他公司总会计师的丈夫等等;一下子涌出众多人物和家庭的命运,让你是目不暇接。虽祖鸿和娇鹂不见,但大家同在河滨大楼这条船上;暴风雨袭来,同船共命。可以说,道是无人却有人。这一平台的构建,为全书后20章的展开是拓开了场子,奠定了基础。
在小说里,有这么个细节,那是一笔笔记下的席秉逊、窦婉芷被抄家的两张《登记清单》。我在朋友的收藏里,见到过求新造船厂1971年抄家类档案,其中一册为《抄家对象郑XX综合材料》。打开第一页,顶天的位置是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在这页《抄家物资处理综合目录》里,1.抄家原因简介;2.抄家物资处理情况说明表;3.抄家原始清单……在《清单》里,仅上海人叫做“黄货”的金器就有:大小金条、金元宝、金手镯、金方戒、金圆戒、金挖耳、牙棒、金领带别针等二十多种。不禁心里感叹,到底是上海人。
我读上海题材小说,更喜欢把它当作了解这座城市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一个辅读,当作欣赏《清明上河图》般的社会生活和风俗的生动直观的画卷。曾在周天籁194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夜夜春宵》里,看到那时不用爬到国际饭店念四层楼顶上,也能看见上海的佘山。上世纪70年代,我在杭州少年宫广场能看到北高峰;在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能见西山。现在望不到的原因,大家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
细节来源于作家的生活积累,展现了他的独特发现。这些看似个体的、细小的、局部的、片段的东西,没有伪装和误导。它以纯真和真实立脚,以自身丰厚多采的积淀立身;它的记录是补白,有启迪。我爱从这里进入上海,读它的今朝和“老里八早”。
无疑,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有着鲜明特色的。总觉得,用上海闲话来讲上海故事才有味道。虽然上海方言受其本身的限制,有些字词难以找到对应匹配并准确传递本义的文字,但这并不是上海话的全部,也不占绝大部。在上海题材的小说中,上海闲话的用与不用,用了多少,用得如何,是对一个讲上海故事作家的考验和挑战。没有“一眼眼”上海闲话的上海题材小说,就像没放苋菜杆的臭豆腐。《魔都》如同《上海霓虹》第一部,作者对上海闲话的运用是娴熟和成功的,这是使他讲上海故事出彩的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
书中写到上海的几处细节,与我了解的有所不同。如写“中百十店(永安公司)”,此时的背景是1965年;而“中百十店”得名于1969年,在1966年改名“东方红百货商店”。又如“延安西路的市委机关”,记得听那时在市委工作的亲戚说:当时是在静安宾馆,门牌属华山路。又,书中的罗老太太咕哝:“杨树浦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这对名词,是要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也有一种说法,在20年代就有“上只角”一词,指的是租界。由来出自地理,因租界在华界南市之上。这些仅供作者参考,把上海故事越讲越好。
与徐策兄相识已久,并曾数年一个食堂吃饭。兄有大志,他告诉我:“据说,已故的文学前辈、名家柯灵、程乃珊等,生前均有创作上海百年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心愿。柯灵先生还在《收获》上发表了开卷第一章,广获赞誉,但未续写下去,成为文坛憾事。我虽不才,天资拙劣,只因出生于河滨大楼这一难得的缘分,加之上世纪80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以后20多年的记者生涯,又有机会深入了解社会方方面面、大范围接触各阶层人士,从而有了些许积累。愿以绵薄之力,写一写我眼中的上海,也算是留下一份微不足道的个人化的城市观照与心灵记录。”
他正一步一个脚印,走向目标。对我而言,除了祝愿,唯有学习。
于2016年国庆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