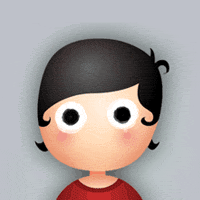从金钱符号到完美情人——杜拉斯的情人三部曲(一)
杜拉斯是法国文坛极具个性的女作家,在她的生命中持久而旺盛地散发着女性荷尔蒙。她以其个人无穷的魅力、不竭的精力与才华给世人留下了才情四溢的精神财富。其实,杜拉斯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浪漫曲折的爱情小说:从少女时期一直到终老,爱情都从未离开过她。惟其如此,杜拉斯的小说作品才处处散发着杜拉斯所特有的爱情的痛楚与诱惑。正是这样一种特质的爱情体验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杜拉斯有过无数的情人,有的是天长地久,有的只是一夜风流。在所有让杜拉斯迸发出创作激情的情人当中,“中国情人”是她反复书写的对象,但这一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年)、《情人》(1984年)和《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年)这三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小说中,我们明显地看到,杜拉斯的“中国情人”形象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之中。最初是丑陋、猥琐的若先生,而后逐渐蜕变成完美的中国北方情人。但在杜拉斯的笔下,“中国情人”只是一个“他者”,作者通过“他者”进行并完成了自我诉说与自我阐释。
2.1作为金钱符号的情人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主要是讲母亲的,在整本书中,贫穷是折磨苏珊一家的挥之不去的灾难。情人只是他们贫穷生活的插曲,他象征着金钱。在殖民地的白人是等级分明的,贫穷的苏珊一家无法和白人社会相容。恰恰由于是白人,苏珊一家又不属于平原上的本地人。有了钱,他们才能真正回归白人阶层。母亲对于贫穷的反抗是积极而隐忍的。在黑暗中为电影院叹了十年的钢琴积蓄了一笔可以反抗贫穷的资金。然而对于贫穷的伟大而盲目的反抗却造成了更可怕的不幸。
“不幸源自那难以置信的天真”。这种天真因为未向租借地管理员行贿而使母亲得到的租借地是一片不毛之地,又使得母亲因此耗其全部精力与财力修筑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在堤坝一夜间被毁后,摧毁了母亲的希望,也让苏珊的少女时期过早的接触到了难以抗衡的不公,母亲被这一切折磨地绝望而盲目。开始寻求一切可以来钱的路子,甚至是女儿。
在杜拉斯的笔下,贫穷是赋予苏珊一家难以摆脱的噩梦。而富有则是他笔下的北方白人种植园主若先生所与生俱来的。若先生的周身散发着的不是男人的魅力,而是着被财富装饰出的华美。贫穷使得苏珊一家对于金钱极为敏感,这个男人手上戴着的钻戒,“这枚被那无知的主人遗忘在手指上的钻戒,其价值几乎相当于平原上全部租借地价值的总和。”而苏珊一家,却为了保住租借地而绝望、崩溃。因此在在他们初次相遇时,男人对自身拥有的财富显露出的那种无知感深深地触动了苏珊,使得她产生了对于这种遥不可及的财富的痛恨。
关于这种贫穷和富有的反差,杜拉斯通过约瑟夫的牙齿和他那辆B12表现淋漓尽致。杜拉斯花了十页的篇幅写关于车的话题,这种有关贫富反差的话语,是通过约瑟夫对于B12的嘲讽式的笑谈展现出来,约瑟夫对于这种生而富有的嘲讽,是由贫穷而引发的无奈的愤怒,和苏珊的反应是相似的。
对于若先生,杜拉斯是这样形容的:
“他妈的。多棒的车呀,”约瑟夫说,然后,他又补充说,“至于其他,活像个猴儿。”
“若先生是这个机智、敏锐的男人的无能、呆笨的孩子,真可笑。他偌大的家产只有一名继承人,而这个继承人却没有丝毫的想象力……”
在这里,若先生的长相被说成活像只猴子,在智商上,若先生被毫不留情地概括为“蠢材”。然而不难发现,这些评价都是基于若先生是个与生俱来的财富拥有者,这种痛恨是基于他们的贫穷,并且是超越种族的。
若先生和苏珊一家产生了联系,他看上苏珊了。对于这样一个有钱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把希望寄托在若先生身上”。因此苏珊一家接近若先生只是为了钱,苏珊由于家中的贫困而自觉地担负起了这个责任——和若先生来往。在这样一个动机下产生爱情是不可能的。贫困始终是缠绕苏珊一家挥之不去的灾祸。过早的接触到贫困,使得苏珊不相信爱情,贫穷也不允许苏珊产生爱情。长期的贫困使得苏珊对于金钱与物品之间的转化非常得了解。对于苏珊来说,一直横亘整个故事的钻石,“它的重要性既不在它夺目的色彩,也不在它的美,而是在它的价值。”苏珊要以最安全的方式获得这枚戒指,只是因为它可以卖很多钱。她的这种想法直接把爱情堵死在若先生未进入苏珊的生活之前。
杜拉斯在《堤坝》这部自传性的小说里扼杀了爱情,苏珊和若先生没有爱情,跟推销员巴尔奈和阿哥斯迪都没有爱情。然而“苏珊不是杜拉斯,完全不是”。因为在《堤坝》里面,情人是偏离杜拉斯的真实的。但是无论是杜拉斯还是杜拉斯笔下的苏珊,都是因对金钱的欲望而与情人相识的。杜拉斯这部小说是关于母亲,更是是关于贫困的,在《堤坝》当中,准确地说是贫困扼杀了爱情。
对于杜拉斯的情人是否真的存在,学界有过争论,现在我们可以证实,中国情人确实存在,他名叫李云泰,并且他的照片也被作为插页照片置于某些关于杜拉斯的书中。透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带有拜伦式忧郁的中国男人。他虽然没有欧洲男性深邃的眼窝,但是他无疑是不丑的。在杜拉斯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得知若先生是一个被她称作雷奥的安南华人。杜拉斯让雷奥披上了白人的皮,变成了白人若先生。我们已经知道雷奥并非情人的真实姓名,对于若先生的丑化是混合着对于因金钱而接近雷奥所带来的羞耻感而施加在她与中国情人的感情中的。巴柔曾明确指出,在个人、集体、半集体这些形象创造者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杜拉斯通过对于若先生的丑化,来宣泄自我,从对于若先生的书写中也看到了一个因贫穷而备受折磨的少女的心。在这点上,这种丑化与社会集体想象的“他者”的形象丑化关系不大。这种丑化是作家个人的、情绪化的表达。
在《堤坝》中,杜拉斯因贫穷而渴望逃离,逃离贫穷,她甚至想让路过的猎人将她带走,此时男人只是作为让她逃离生活现状的一个工具。
杜拉斯的《堤坝》与爱情无关,但是通过“情人”,杜拉斯开启了欲望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