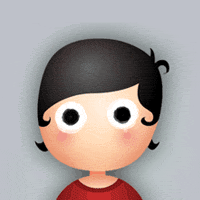萧声尽15
上海,三山公馆。
最里面那桌麻将声响个不停,洪八嘴里叼着烟,洪太太何兰芬笑眯眯地坐在他身后,她比婚前丰满了些,脸庞圆润,看上去温婉可亲,都没想到这样一个霸王样的人教个女学生给降住了,有人便说这女学生来历也不简单,她爸爸是如今上头哪位的恩师,洪八攀上这位将来是有大好处的,又有人说听说这个女学生是从家里私奔出来的,老丈人根本不承认这个女婿的存在,因此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这些话传来传去的就没有意思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倒是越来越好。
“不累么?”洪八摸着肩膀上的小手,“闷得慌就出去走走,这圈马上就打完了。”
“原来这就是你的太太呀,”兰芬还没说话,身后便传来银铃般的笑声,“比你强多了,你可真有福气。”
兰芬侧转身,看见身边站着一对璧人,男的穿着一身中山装仍旧盖不住通身的军人气质,女子小巧玲珑,眉目如画。
桌边另外三位认得张启山,其中一个便站起来让位置,“走,咱们俩去花园逛逛。”新月拉起兰芬的手。
“好啦?”洪八这一句问的旁边人甚是莫名其妙,张启山却是心里明镜似的,“好了。”他笑笑,开始码牌。
廊下左边就是花园,晚间看上去那里有些阴森可怕,虽然几盏西洋式样的路灯在里面点缀着,她们两个便在回廊里的椅子上坐下,服务生殷勤地送上饮料。
远处的一个桌子边坐着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面对面坐着窃窃私语。
“谢谢张夫人送的礼物。”兰芬先开了口,“我家那位还说要去长沙看望你们俩,可惜一直没抽出时间来。”
“我倒没想看他,我就想看看你长什么样,”新月笑眯眯地说,“那天洪八爷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都放光了。”
“那天张长官给我家那位来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呢,听得清清楚楚。”兰芬觉得这个女孩心直口快,便也逗她,“他说什么了?”新月果然当真,脸一下子就红了,呐呐地问。
“他说啊,只要让你高兴,他就是倾家荡产也乐意,”兰芬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她的反应,“你可真狠心。”
“怎么你们都知道了。”新月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这不挺好吗,没有考验,怎么知道你们到底合不合适。”兰芬抿了口果汁。
新月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也喝了口果汁,觉得比北平自家的还要甜些。
远处坐着的两个男人其中的一个起身离开。
“那,你家那位当初怎么追你的?”新月眼睛亮亮的,充满好奇。
“他...”兰芬想了想,过去种种流水一般从心头掠过,五年前自己对他确实是没有一点印象,他却把自己当成生命中唯一的一束阳光,缘份实在奇妙,“他喜欢了我五年,我现在才知道。”毕竟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幸福如果不能和人分享,未免遗憾。
果然,新月的眼睛瞪圆了,“真看不出来,他那么痴情啊。”
看着兰芬由于幸福而更加容光焕发的脸,她由于怀着同样的感受而觉得她分外可亲可爱,一时想做点什么来纪念她们的的相识,手上除了二响环也没戴什么首饰,突然心里一亮,想起小时候和女友经常做过的事。
“咱们交换耳坠子罢,”她愉快地建议,“他们两个是好兄弟,咱们俩就是好姐妹了。”
兰芬没有意见,她随即取下耳朵上的红宝石耳坠子,戴上新月的珍珠耳环。
“我以后就来找你玩啊,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新月耳边的一缕碎发缠住了耳环,兰芬伸手帮她绕开。
“我每天就在家里,很少出去,”兰芬说,“他平时挺忙的。”
“我在长沙的时候也是这样,”新月嘟起小嘴,“要是咱们俩住得近点就好啦。”
兰芬觉得和这个稚气未脱的张夫人无端亲近之感,她刚要张口,突然微微变了脸色,拉起新月的手,低声说,“进屋去,快。”
新月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好。”
偏偏这个时候鞋子细细的高跟卡在了铁丝桌脚里,她用力拔了两下才拔出来,这时留下的那个西装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踉跄着向这边走过来,新月一回身正好和他站了个面对面,看见那人捂着左胸,手指缝里正汩汩冒出鲜血,吓得头发都立起来了,但是还知道控制自己不要大声叫喊,只是全身剧烈地发着抖。
那人表情痛苦,努力地张开嘴想说什么,一阵剧烈的痉挛使他向前跪在地上,新月向后退了两步,她想跑,却不知怎的脚下生了根,兰芬此刻倒是冷静了许多,她低声地问那人,“你是想告诉我们凶手是谁么?”
那人用最后一丝力气抬起头,艰难地摇了一下,抖抖索索地伸出一只带着血的手,却是向着新月,想要递给她一样东西。
新月被周围弥漫的血腥气和这人垂死的眼神惊着了,只知道盯着那只带血的手看,身子却一动不敢动。
那人已经濒临死亡,只是最后这一个动作吊着他的一丝力气,一旁的兰芬觉得不忍,伸手接了过来,那人轻轻叹了口气,好像有些遗憾,又像是终于放松了,随即向前一扑。
“你认识他?”兰芬低声问。
“不认识,从来没见过。”新月声音发着抖。
“没事,快走。”
兰芬拉着新月紧走几步回到小客厅,新月的心突突跳地厉害,出门撞上这个真是不吉利,回头得让张启山陪她找个寺庙拜拜,新月想。
“人走时气马走膘。”洪八看着张启山跟前堆成小山的筹码,后者笑笑,拿出一个递给侍应,“去看看两位太太去哪了。”
侍应答应着要走,这边太太们已经手拉手回来了,与此同时,外面传来一声尖叫,“杀人啦!”
张启山看见新月的脸色便知道她可能碰上了什么,这局牌自然也是打不成了,“在租界杀人,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洪八小心地护着老婆跟着人流往前外走。
新月跟着他懵懵懂懂上车回到住处,张启山让她坐在沙发上,又给她倒了杯热茶,才问,“怎么回事?”
“那人就死在我们面前,”新月惊魂未定,“兰芬胆子可真大,”她缓过劲儿来,感觉身上的旗袍都沾上了血腥味道,“这衣服不要了,”她站起身换下旗袍,“我都快被吓死了,她还问那人要干什么。”
“既然已经碰上了,就走不了,”张启山说,“你有没有看见凶手的脸?”
“离得远没看见,不过...”新月努力地思索着,“那人好像,走路有点重心不稳,站起来的时候向右倾斜了一下,我当时还想怎么就喝多了,后来看见他们桌子上摆的是咖啡杯...你盯着我干嘛?”
“你这衬裙怎么这么薄。”
“讨厌,”她推着他的手,“人家心还在砰砰跳呢,你还有心思想这些。”
“有个法子能让你不害怕...”
她半推半就地地阻挡着他的手,门被轻声敲响了,“夫人,”双喜如今也改了口,“中统那个姓杨的又来了。”
“你说那人走路颠簸,可能是腿不一边长,还有可能是受伤了。”洪八说,“拿来我瞧瞧。”
兰芬伸出手,掌心是一枚女式的宝石戒指,做工很精巧,洪八拿过来端详了一阵子,撂在一边的茶几上。
“也不知道她怎么认识的那个人,找个机会扔了罢,留着也是麻烦。”兰芬说。
“听说是个记者,”洪八说,顺势把兰芬拉过来坐在怀里,大手放在她的腹部,“刚才没吓着你罢?”
“我还好,倒是把张夫人吓得够呛,脸都白了,”兰芬轻笑道,“可能是你儿子胆大罢。”
“还有七个月就熬出头了。”洪八喃喃自语,“你算什么呢?”兰芬奇怪地问,忽然明白了,不由得脸上飞红。
洪八不回答,只是把头深深埋进她的怀里,像孩子索求温暖一般。
双喜站在赌场的一个角落里,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一切尽在眼底。
张启山走向吧台,一个穿着风衣的男子背对着他坐在那里。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乱世吗?因为只有在乱世才能放肆的显现自己的本性,没有规则,也无需隐藏,人性充分的暴露。”杨立仁轻轻晃动一下手里的杯子,琥珀色的液体荡漾着,折射出迷人的光。
“你的话和你的行为正好相反。”张启山也坐下来,点了一杯鸡尾酒。
“是啊,所以人要同时具备感性和理性,”杨立仁举起酒杯,“欢迎回到大上海。”
“你一贯无事不登三宝殿,”张启山和他碰了一下,“来干嘛?”
“想跟尊夫人谈一下。”
“不行。”张启山斩钉截铁地反对。
“你不必如此紧张,不是上次的事情。”“什么都不行,我不想她再跟你们有任何牵扯。”
杨立仁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嘴角露出一丝讥笑,“你希望换个人来,还是换个地点?”
张启山被他的口气激怒了,把手里酒杯一顿,酒水溢了出来。
他的手被一只小手轻轻按住,新月看了他一眼,又对着杨立仁说,“你想在哪儿谈?”
“两小时前,三山会馆,你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请如实回答。”楼上一间小客厅里,杨立仁和新月面对面坐着,他的脸上换了一副表情,既冷漠,又似乎随时准备着捕捉对方话语里面的感兴趣的东西。
就像一只准备捕猎的豹子。
张启山站在窗口,楼下是花园,铁栏杆外有两个人在那里抽烟,眼睛却不时往这边瞟一下。
新月仔细地思索着,“我当时在和朋友说话,所以没有注意到那两个人的长相和年龄,只记得先离开的那个人有点跛脚。”新月说。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离得太远,听不到,”新月说,“我根本没注意他们,也不明白那人为什么直接就冲着我过来了,还...”
“还什么?”杨立仁敏感地追问,目光如隼般集中在她的脸上,她被他看得一哆嗦,张启山不满地走过来,“你别这么问她。”
“此事涉及范围甚广,张长官恐怕抗不起来,”杨立仁的目光充满狂热,“那人做了什么?”
“他...”一滴汗水从她的头上慢慢滑下来,“他当时应该是想说话,但是已经说不出来了,满手是血,特别吓人。”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发着抖,求助似地看向她的丈夫。
“可以了,到此为止。”张启山几步走到她身边,口气不容分说地搂住她的肩膀站起来,杨立仁站起身,却也没有做出阻拦的动作,“这一周内如果您想起了什么,”他向张启山一点头,“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
“你太过分了。”张启山冷冷地说。
“我是在帮你,”杨立仁口气十分强硬,“作为高级卷进这种事情,不算脸上贴金。”
那就是说这一周都不能离开上海了。新月想问她的丈夫,又想起听别人说过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中统找谈话,这场风波毕竟因自己而起,便决定不问了。
只是那个男的之前她并未见过,为什么临死前要找上自己呢?
现在也不敢去问兰芬,自己已经被中统讯问,不能再连累了她。
张启山见妻子被问话之后变得很安静,也知她心情郁闷,强行离开并非不可,但是对方如果一本参上去,把自己的部队调到江西或者贵州,既合了上头的意,又削了手里的权,那可是大大的不合算,便回过头来安慰她,“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事,呆一周也无妨。”
新月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怎么了?”张启山把她搂过来,“别怕,有我呢。”拉着她的手走到窗口,“你看这外滩,也是新月形的。”
新月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
“别想太多,”张启山抱紧了她,楼下不远处传来一阵哨声,随即看见穿着黑制服的巡警骑着自行车远远而来,“这大上海每天都会死几个人,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他只问那个死者临死前的细节,而并没有问凶手。”过了一会,新月随口说了一句,随即意识到了什么,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
“别再想了。”张启山试图安慰她。
“我刚刚跟他撒谎了,那人临死之前确实给了我一样东西,”新月鼓起勇气,转过身直视着他的眼睛,“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怕他们不相信我。”
“什么东西?”
“我没敢接,兰芬拿过去了,是一枚...戒指。”
“你确信之前没见过那个人?”张启山声音里隐隐透出一种怀疑。
“连你也不相信我了!”新月委屈地几乎要哭出来,一甩手挣脱开他的怀抱,“我干脆跟他说清楚好了,到时候大不了把我抓起来!”
张启山一把拉住她的胳膊,任凭她怎么挣扎就是牢牢抱着不撒手,“我不是不信你,”他在她耳边低低地说,“我是怕你有危险,有的时候你可能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你,你好好想想,真的以前没见过他么?”
“真的,”新月一口咬定,“我别的不行,过目不忘的本事还是有的,在新月饭店的时候,谁也别想在我跟前抖机灵。”
“那就奇怪了,”张启山喃喃地说,“他到底是冲着谁来的呢?”
“会是冲着你么?”她担心地问。
是我倒好了,他收紧了胳膊,用力搂着她,下巴一下一下蹭着她的头顶。
他从后面抱住她的时候,下巴正好搁在这个位置,不知不觉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没关系,明儿个派人去打听一下。”他松开手走进浴室,很快便传来了哗哗的水声。
“泡个热水澡就好了,”他走回到她身边,“也不知道水热不热...没你家下人伺候的好。”
见她终于笑了,他也如释重负,“没事,他们中统一贯小题大作。”
“他们肯定在监视咱们,这个时候派人去调查...”“当然不用我出面,让洪八去,”张启山说,“现在咱们两家是在一条船上了。”
一泓池水包裹着她的身体,她闭上眼睛,努力想把刚才的事情忘记,却止不住回想起那人染血的手,以及兰芬沉着冷静的面容,尽管水很温暖,她依旧止不住微微抖。
门被轻轻地敲了两下,没等她回答便开了。
“谁让你进来的。”她慌忙躲到一边,看着那门一点一点地打开,门口却空无一人,她的头发根都立起来了,象被定住了一般一动也不能动,睡衣就放在一边的篮子里,却不敢伸手去抓。
眼看着她就要哭出来了,突然就从外头窜进一个人来,“吓一跳罢!”
新月小脸煞白眼里噙着泪,见到他如同看见救星,先是一惊,继而一身是水地扑到他怀里。
“害怕的时候吓上一跳,就什么都忘了。”那人抱着软玉温香细细地用毛巾擦着,一边大言不惭地解释着刚才的行为。
“胡说八道!”小媳妇儿终于缓过劲儿开始炸毛,抡起粉拳就是一顿捶,“你就是想占我便宜...不要脸的...”
“我哪没见过...害什么羞又不是大姑娘...”“流氓!”她气得不行,“你给我出去,我饿了!我要吃夜宵!”
当一种本能遇上另一种更为原始的本能时,谁会先让步呢?
几分钟后,张大佛爷端着一碗酒酿赤豆元宵笑咪咪地敲响了张夫人的房门。
“她的话里有一些东西,让我想想,”杨立仁在屋里踱着步子自言自语,“满手是血,她为什么不说满身是血?他的手里...到底有什么?”他快步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
“跟她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他脸色有些阴沉,“他洪八跟土匪拉拉扯扯不是一天两天,...不,先不要惊动他本人,会很麻烦。”
他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怎么办?”床上,他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会把那幅飞禽图给你烧了,”史秀珠茫然地说,“李煜的。”
他突然发出一阵神经质的大笑,“没想到你也会开玩笑啦。”
街头一个热闹茶馆坐满了茶客,他们和其他地方的茶客一样谈天说地,上至时局股票下到鸡毛菜的价格,只是偶尔某个人看似不经意某个动作,茶碗一摆,或者手掌一翻,便传达出了某种特定的含义。
“那就是洪门在盘海底,”汽车里,一个看上去很精明的年轻人低声说,“这两天他们活动十分频繁。”
“要不要抓起来问问?”司机问,同时回头邀功似地看着暝目养神的头儿。
“抓个屁!”中统行动大队队长潘大有忍不住骂道,“抓谁?青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真听了你的,提篮桥都装不下!”
“那...怎么办?”
“勤盯着,总能看出点什么来,另外你们在洪门里头的暗线呢,不能光吃饭不干活。”
“头儿,到底丢了什么东西?”先前说话的年轻人问。
“多干活儿,少问问题。”潘大有叼着烟,漫不经心地说。
“总的知道找什么呀。”年轻人不甘心地补上一句。
“一个胶卷。”潘大有吐出一口烟。
“那人名叫孙楚瑜,申报记者,左翼人士,半年前来到上海,”洪八向前倾过身体,“你老婆...当真不认识他?”
张启山脸终于撂下来了,“她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还不乐意了。”洪八拿出一张报纸拍在他面前,上面是关于新月饭店历年进行慈善活动的一篇采访,上面刊登着新月父女的大照片,记者署名赫然是孙楚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