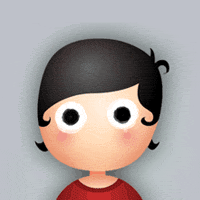浮梦醉|十二濯香令之错相见 —语笑嫣然
图源/网络
十二濯香令之错相见
文/语笑嫣然
摘要
诸葛正扬看见了,看懂了,他亦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深深地盯着靳冰越那双清澈的眸子。
似是在说,你知道原因的。
是因为痴爱与迷失。
奋不顾身地去做错。
紫衣
暮秋时节。原本就冷清的长风镇,显得更加寂寞萧条。蜿蜒的提柳街,一路都是铁匠铺子。铁匠们老少胖瘦参差不齐,但却都在打量着一名穿紫衣的少女。那少女生了一双灵巧的小鹿眼睛,眉弯浅浅,美人尖,瓜子脸,唇如樱桃,肌若白雪,怎么看都是纯善乖巧的富贵模样。她背着粉色绸缎的小包袱,手里没有任何防身的兵器,大步流星地沿着提柳街走,全然不在意铁匠们诧异或者猥亵的目光。
走到尽头。
在一面旧得发黄发黑的布幌子底下。少女站住了。盯着火炉前光着膀子的铁匠喊:"你是不是蓝冲?"那铁匠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高而健硕的身形,皮肤暗沉,眉目俊朗,表情带着戏谑与轻佻。他懒洋洋地笑道:"正是。"
话音刚落,却见少女一个轻盈的起身,稳稳地落在面前。然后右手像锋利的鹰爪,揪住自己胸前的衣襟,作势要扯开。出于本能蓝冲挥手挡了挡。可他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实在没什么收效。反倒使自己撞在石台边缘,痛得哎哟哎哟的愁坏了脸。一边还嚷嚷地喊:"虽然我蓝冲在这长风镇是出了名的美男子,但姑娘要和我洞房,也不必如此粗鲁吧。"
"无耻--"紫衣少女狠狠地骂了一句。但忽然觉得背后有一股强劲的力道长驱直入,正待回头,手腕已被扼住。她立刻朝着蓝冲的脑门踢了一脚,借力使自己凌空翻身,挣脱了那来历不明的攻击。待到双脚重新落地,再看,只见水缸旁边多了一名穿着整齐的白衣男子,正笑微微地望着她,然后朗声道:"姑娘何以为难我的朋友?"
"与你无关。"少女显然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又扬了扬脸,问道:"你是谁?"
白衣男子收了对阵的姿势,极有礼貌地作揖:"柳生门,诸葛正扬。敢问姑娘芳名?"少女噘起嘴,不屑道:"原来是柳生门的人。"刚说罢,撇了一眼摔在墙角的蓝冲,拂袖而去。
温柔乡
长风镇方圆几百里,都在柳生门的势力范围。要追查一个人的身份来历并不难。因而诸葛正扬便又去了铁匠铺。
蓝冲以珍藏的好酒相待。
一点也不吝惜。
只道:"蓝某能识得诸葛兄这样的朋友,此生也不枉。"
诸葛正扬端起酒杯,嗅着扑鼻的醇香,道:"蓝兄最近可是得罪了什么人?"蓝冲愕然:"诸葛兄是指前两天来闹事的那位姑娘?"诸葛正扬点点头,呷了一口酒,沉声道:"靳冰越,她是红袖楼的人。玉罗七小主之一的灵蛇小主。"
说罢,蓝冲显然是紧张起来,不做声了。
那灵蛇小主靳冰越对江湖中的事情了若指掌,就好比一部活生生的百科典籍。她的兵器--柔丝索--细如牛毛,软如灵蛇,乃是一条极为坚韧的银丝线,最短时,可盘于左手无名指的戒指里,最长时,可挥舞如利箭如刀剑如长鞭,断人头颅割人咽喉都并非难事。
然而,蓝冲却想不明白,谁会舍得花重金雇佣红袖楼的人来找他这样一个小铁匠。她是要砸了他的生意呢,还是绑架他,折磨他,取他的性命呢?
当中的原因,靳冰越自然也不清楚。她只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整个红袖楼,亦是从来不过问为什么。
只管,怎么做。
但难就难在蓝冲名不见经传,靳冰越从未听说过这号人,只是雇主说蓝冲两年前曾在粤北一带,她便从扬州南下而来。--寻人,也是她所擅长的。一路上,她见了四五十个名字叫蓝冲的年轻男子,有种田的庄稼汉,也有脑满肠肥的奸商,可是他们的胸口都没有刀疤。她要找的蓝冲,在胸口,有一道两寸长的疤。
那会不会是轻佻的铁匠呢?
靳冰越的嘴角浮起一丝冷笑。丫鬟已经把薄如蝉翼的衫子拿过来,披在肩上,露出白皙的藕臂,光洁的锁骨,可以看见胸口饱满的突起,腰间盈盈一握的纤细,那消魂的模样乐得老鸨直拍掌,道:"从今后你便是我金香楼的头牌姑娘,好好地伺候客人,我必定不会亏待你。"
靳冰越连眼皮也懒得抬。
她不过是知道了蓝冲最爱流连烟花地,是这金香楼的熟客,因而想肆机接近他,看他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找的人。--有时候,名不见经传,却未必能够大意。况且,这里是柳生门所管辖,她也须谨慎小心。既然柳生门的大弟子诸葛正扬与蓝冲交情匪浅,她若再强行出手只怕又要生枝节,倒不如悄悄地隐身在这温柔乡,为对方筹备一席精致的鸿门宴。
未几。蓝冲果真是来了。换了简洁整齐的衣装,没了铁匠的粗犷,那模样颇是挺拔轩昂。但眉眼间总是带着轻佻戏谑,堪堪地,便将气质折半。
靳冰越掀开帘子施施然地走出去。
蓝冲一抬眼,便僵住了。虽然还是淡紫色的衣裳,可香艳的脂粉却透露出消魂的魅惑,迷离的眼神就像光滑的丝缎,温柔地拂遍全身。蓝冲甚至忘了害怕,结结巴巴道:"是,是你?"靳冰越挑眉一笑,道:"可不就是我了。"
"你,你是故意在这里等我?"
三两句话,靳冰越已经走到蓝冲面前,右手搭着他的肩膀,踮起脚尖呵气如兰,道:"我只想证明你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如何证明?"
"让我看看你的胸口可有两寸长的伤疤。"
"啊?"蓝冲脸色骤变,推开靳冰越退至墙角,那激烈的反应仿佛是承认了他的胸口正好有那道伤疤。靳冰越顿时卸去那虚假粘人的伪装,瞪着蓝冲。
蓝冲连连摇头:"没有,我没有伤疤。"
"如若没有,何苦不肯亮出证据来?"靳冰越说罢,冷哼一声,扼住蓝冲的咽喉,戒指里如春蚕吐丝般飘出一缕银白的丝线,却像厚重锋利的刀,将蓝冲胸前的衣服割开一道。
伤疤。
两寸长。
清晰分明。
慌乱中,蓝冲抓到盆景里一块假山石,可那石头纵然吃足了劲,却也没碰到靳冰越的衣角。而是从窗口飞落在大街上。
啪啦。
裂成了两半。
行人的吵嚷漫骂,也掩盖不了心跳的巨响。蓝冲狼狈地逃窜,仍是不甘心,呼喊道:"你究竟受了谁人的指使,何不告诉我,让我也死得明白。"靳冰越不耐烦地拂了拂戒指:"谁说要你死了,我不过是要将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正说着,突然,一枚飞镖擦过鼻尖,嵌了半截在雕花的木窗格里。随即便听见诸葛正扬的声音,似还在楼下大堂,可是转眼却将门破开。
电光火石间,靳冰越只感到眸子里一阵沁凉,忽而又是灼烫如炭烧,所有的光亮在瞬间熄灭。天地仿佛都化做黑暗的泡沫。
刺骨锥心的疼,席卷蔓延。
她瘫软在地。片刻之前的嚣张气焰,顿时溃散。
变故来得太快,在场的人,甚至诸葛正扬,也没有料到自己的飞镖会恰好伤到靳冰越,那样不偏不倚地,将清漾漾的眸子割出两道血红。
他震住了。
蓝冲亦是愕然惊呼。
靳冰越死死地握着拳头,却扼不住表情里的惶恐,只是倔强让她一直强忍着,她放开了手里的柔丝索,挥舞着,歇斯底里。鲜血汩汩地溢出眼眶,爬满白皙的面颊,沿着脖颈,红了单薄的紫衣。那模样,不是肃杀,狰狞,而是无助。
变得楚楚可怜。
老乞丐
靳冰越逃出了金香楼。逃到一处荒僻的,散发着霉味的茅屋。双膝一软,载倒在地。
两眼又是狠狠的一阵疼。
她什么也看不见了,不知道自己是向着哪个方向逃,逃了多远,多久,也不知道诸葛正扬和蓝冲有没有追着她,她已然精疲力竭。渐渐地昏睡过去。迷梦中仿佛又回到金香楼的一幕,追逐和闪躲,猝不及防的暗算。
仿佛又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诸葛正扬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夜深凄寒。
她蜷缩着像尺蠖,抱紧自己,泪水冲开了凝固的血迹。就那样,时而发热时而发冷,不知道睡了多少个时辰,最后终于醒了。可是,再也不像从前,睁开眼睛,已经看不到半点光亮。她舔了舔嘴唇,退到墙角。
仿佛是背靠着墙壁,才可以感觉到一丝安全。
这时候,她听见一阵细碎的响动。她忍了哭腔,厉声喝问:"是谁?"过了半晌,才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回答说:"小姑娘,你占了我老乞丐的位置了。"
此后,靳冰越便在茅屋里住下来。或者说,是借了片瓦遮头,却将身体隐匿在最黑暗的角落。她问老乞丐,有阳光照在我身上吗?老乞丐说,有,她便颤抖着向别处挪去,然后再问,有吗。直到老乞丐告诉她,她成了一团黑糊糊的连影子也看不见的烂泥,她才心满意足地静坐下来。
老乞丐偶尔会笑话她,说:"姑娘,人生在世,并非一定要光鲜才有快乐的,像我这样破烂的乞丐,也一样能活得逍遥自在。"
"可是,我的情况和你不同。"靳冰越怅声喃喃。
老乞丐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只鸡腿,香气顿时溢满了小茅屋。这大概是他最近带回来最昂贵的一件乞讨所得了。他看着靳冰越狼吞虎咽的模样哈哈地笑起来。他的笑声像是极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带动着靳冰越也牵了牵嘴角,虽然是似笑非笑,但也算是大有进步的表情。
某天,老乞丐兴高采烈地回来。告诉靳冰越,他从江湖朋友那里打听到,原来花蕊夫人正隐居在丹霞山。靳冰越立时来了精神,道:"可是那曾用金针为烈狱门门主医治眼盲的顾家传人?"据说当年烈狱门主的双眼为仇家所毁,经脉尽断,目不能视,但花蕊夫人却只用几根金针便使他复明,顾家的金针因而名声大噪。初时靳冰越曾想过,若能找到花蕊夫人,自己或许能有几丝复明的机会。可她眼下却受困于此,举步维艰,更谈何外出寻人。
已然是有如溺毙在深潭。
幸而她遇见老乞丐,像遇见一只桨,一条船,将她拖拖拽拽地引到岸边。她从来没有想过破落的乞丐也能成为自己的贵人。她激动起来,抓住了老乞丐的手,道:"老人家,谢谢你。"那臂膀沉实而温暖,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悄悄地蔓延开。
老乞丐慈祥地笑着,说:"反正我走到哪里也是乞讨,不如将好事做到底,陪你走一趟丹霞山吧。"
长风镇离丹霞山并不太远。纵然靳冰越行动不便,有老乞丐的照料,也最多三五日的行程便可到。只是一路的磕磕绊绊倒真是不少,连路边的小石子也能踩上去滑一跤。手和膝盖都磨破了,青一块,紫一块,老乞丐便用草药给她敷着,冰冰凉凉的,疼痛很快减轻了不少。
夜里,错过了驿站,唯有露宿。
靳冰越问老乞丐:"老人家,这附近是怎样的景色呢?"老乞丐说,有漫天星子,黝黑起伏的远山,稀松的丛林,近处是一片鹅卵石的野地,开着白色的小花,就像铺着融融的柳絮。他说:"你吸一口气,就能闻到野花的芬芳。"
靳冰越怔了怔,忽然问:"你真的只是个乞丐么?"
繁花
当然,不是。
只不过知道得太迟。
当他们找到花蕊夫人,并且说服了她的恻隐心,答应出手医治,老乞丐便悄悄地离开了。那清晨蒙蒙的雾气濡湿了缠着纱布的眼睛,靳冰越问花蕊夫人:"老乞丐去了哪里?"
花蕊夫人诧异,道:"何来的老乞丐?"
靳冰越眉心一抖,道:"昨日送我来小筑的那位老乞丐啊。"
花蕊夫人便笑了,道:"人都说,眼盲心不盲,姑娘莫非从来没有怀疑过,他那把苍老嘶哑的声音,其实是故意伪装的?他临走时虽一再的请求我为他保守秘密,但我却是不忍心看他浪费了一腔真情意,他的神态动作,无时无刻不在泄露着他对姑娘的温柔与关切啊。"
一语道破。
实则靳冰越何尝不曾怀疑过,那恰好出现的老乞丐,总是能给她温暖照顾的老乞丐,怎么会那样稳妥地牵引着她,重拾生的希望。她扶过他的手,是粗壮有力的臂膀,平整紧绷的皮肤;她窃听过他的脚步与呼吸,是铿锵而掷地有声;她还嗅到他的乞丐装带着清新的布料香,没有发霉或酸臭;一切的一切,就好像是在隐藏之余还要故意显露。
那昭然的关心,温柔的迁就,如何是一个老乞丐所能给予。
而靳冰越,又如何能不怀疑。
只是,她默默地承受着,尽量使自己不去深究,因为在她的心里总是有个模糊的影子,她并不希望那影子会突显。
突显到现实里。突显到面前。
她宁可她所遇见的,真的只是一个邋遢佝偻的乞丐。
但如今花蕊夫人却将真相挑明,她已然无从逃避。她一边摘下药味刺鼻的纱布,一边问:"您可认得那个人么?"花蕊夫人摇头,道:"虽然他将自己弄得蓬头垢面,却也不难看出是个英俊的少年,而且,眉眼里总是含着笑。"
说罢,纱布的最后一圈也解开了。
光线从四面八方穿透,像无数的萤火虫,钻进瞳孔。连心也跟着飞舞了起来。
她又能看见东西了,红的花,绿的树,天苍地阔,影影绰绰。她握着花蕊夫人的手几乎要感激得大哭一场。花蕊夫人端庄的一笑,道:"姑娘,此后的一段时间,你的眼睛会出现失明与复明交替的症状。但你无须担心。因为每次失明都是暂时性的,一两天之后便可不药而愈。大约有了三四次那样的反复以后,你的眼睛便可彻底康复了。"
"是的。我记住了。"
靳冰越恭敬地向花蕊夫人致谢。也不再多做逗留,便离开丹霞山,回到了长风镇。
长风镇上的铁匠铺子没有丝毫的改变,黑黝黝的年轻铁匠仍是埋头苦干着,听见脚步,也不抬头,只懒洋洋地问:"客官想要铸刀还是铸剑?"
靳冰越站定了,冷冷说道:"要一对眼珠。"这句话比发射一枚暗器更可怕。吓得蓝冲直往后跳,盯着靳冰越,结巴道:"姑娘,你,你的眼睛?好了?"
靳冰越轻轻地咬着唇,忽然,一抬手,那纤细锋利的柔丝索便搭上了蓝冲的肩膀。她道:"你既然早知有今天,当初何必救我?"
"我?"
蓝冲瞪大了眼睛。半晌,狠狠地将头一低,道:"看来我是难逃此劫了,只请姑娘动手的时候利落些,好使我少些痛苦。"说罢,一阵风吹开了炭炉上的火星。那些跳跃的精灵如若换成白色,会不会就像是漫天星子?
又或是野地的繁花?
尽虚妄
在那一刻,无论蓝冲还是靳冰越,都没有想到,重逢只是一场峰回路转。柔丝索并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它又乖乖地缩回戒指里。而戒指的主人,愁眉深锁,香肩发颤,呆滞地站了半晌,最终拂袖而去。远远地听见背后还飘荡着铁匠愕然的声音:
"姑娘--"
她没有回头。
究竟是怎么了?靳冰越问自己。为何从前可以杀人不眨眼,方才却迟迟狠不下心,仿佛自己面对的是世间最珍贵的艺术品。
不能破坏。奉若神明。
难道仅仅是出于感激?感激对方这些天默默的照顾,感激他给她机会重见光明?可是,若不是因为他,她根本无须忍受失明之痛啊。说起来他根本就是罪魁祸首,怎么反倒变了出手拯救的英雄?靳冰越想着想着,挥出拳头,隔空斩断了一片大树的枝桠。
漫天落叶飞舞。
寂寞萧瑟。
她在荒凉的湖畔坐下来。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夕阳铺满金色的鳞甲。碎碎点点,就好像铁匠铺里漫天的火星。她仿佛又看到蓝冲,他专心而汗流浃背的模样,他嬉皮笑脸玩世不恭的模样,他慷慨凛然毫无惧色的模样,还有他假扮的嘶哑,低沉,温柔关切。
渐渐的,靳冰越感到视线模糊了。天边尚有夕阳的余晖挂着,她却再度什么也看不见了。但她并不惊慌。因为花蕊夫人说了这将只是暂时性的失明。她便屈膝坐着,很努力地回想数天以前在茅屋里的情况。她试着描绘蓝冲穿乞丐装污秽邋遢的模样。然后忍不住轻轻地笑起来。
突然--
靳冰越感到有一双温暖而沉实的臂弯从背后环过来。她周身猛地一颤。想要挣开。可是却在抓到对方的手的时候,愕然地僵住了。
那是她熟悉的触感。
似乎就连皮肤的纹理也清晰可辨。
这不是一路相伴的老乞丐吗?这不是她心里正想着的蓝冲吗?她的心顿时跳得飞快。她有那样多的话想说,有那样多的疑惑等待解答,可是,却遭到对方唇舌的封锁。她感到不知所措,就好像飘在云端,喝醉了,身体不由自主地迎合起来。
她已经分辨不清什么对错道理。
她彻底地沦陷进去。
翌日清晨。
靳冰越怀着身体轻微的疼痛醒过来。睁开眼睛,柔和的光晕照射覆盖。她的眼睛果然如花蕊夫人所说,重又恢复了。
她听见背后均匀酣畅的呼吸。
顿时羞得满脸通红。
--昨夜,造就了她生平最快乐的时光。她在那场彻底的交付里面看清楚了自己的心中所向。原本笼罩着的阴郁和迷雾,都豁然开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凤飞翱翔,四海求凰。执子手,与子老。前人所有所有的佳句,她瞬间明白。
她眨了眨眼,娇笑着,缓缓地转过身去。
可是。
突然。
犹如晴天霹雳。
靳冰越浑身都僵硬了。她看见的,并不是蓝冲。而是,而是诸葛正扬。
那时候,靳冰越终于知道了真相。原来,假扮老乞丐照顾自己的是诸葛正扬。费尽苦心查探到花蕊夫人下落的,也是诸葛正扬。
从始到终,和蓝冲有关的一切,都是幻想。
是她一厢情愿的假象。
诸葛正扬酣甜地睡着。嘴角带着笑。也许是还停留在消魂的美梦里,却突然感觉到脖子一凉,骤然惊醒过来,只见靳冰越正用柔丝索扼着自己的咽喉。他面色一沉,道:"我早知你恨我。但是,我却无法压抑自己的感情。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便已经爱上了你。"虽然诚恳真挚,但在靳冰越听来,却仿佛是侮辱。
是伤口上撒盐,是雪上加霜。
"诸葛正扬,我要杀了你。"--这是靳冰越对昨夜温存过的男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无爱有恨。成千古的定局。再也无法扭转。
说完那句话,靳冰越将柔丝索绾出一朵艳丽的花。
对准了诸葛正扬的心脏。
痴爱
若论武功,靳冰越不及诸葛正扬。哪怕是柔丝索离诸葛正扬只有两寸远,他依然巧妙地化解开。只是伤了皮毛。
逃了。
靳冰越扯着凌乱的衣衫,呆呆地站着,看着她所痛恨的背影消失在树林的尽头。她感到浑身瘫软无力。这时候,天空下起雨来。豆大的雨点,很快淋湿了全身。她就那么笔直地站着,仿佛期待这些天降的甘霖能够洗清自己的污秽。
可是,烙在记忆里面的,还能洗么?
靳冰越极尽疲惫地走回了铁匠铺子。蓝冲看见她,虚弱的失魂落魄的模样,虽然仍有些害怕,但依然给了她一碗热茶。
说道:"姑娘,喝了暖暖身子吧。"
靳冰越顿时泪落如珠。
胜过屋檐滴滴答答的雨帘。
后来,靳冰越没有告诉蓝冲她和诸葛正扬之间发生的事情,只是很无奈地摇头说:"我就要离开长风镇了。"
蓝冲显然有点着急,道:"你回去如何向雇主交差?"靳冰越似笑非笑:"难道你真要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呃,当然不是了……"蓝冲鼓了鼓腮帮子,示意自己不再多言。那模样看起来就像是顽皮的幼童。
雨渐渐停了。
蓝冲忽然感觉到一阵莫名的眩晕,踉跄几步,便昏昏沉沉地倒在了地上。这时,靳冰越的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她轻轻地将一根很细的竹筒插回腰间。
那是她惯用的迷香。对付像诸葛正扬那般的高手,或许派不上用场。但对付蓝冲,已是绰绰有余。
稍后,靳冰越收买了一名乞丐到柳生门传话,是以蓝冲的口吻,就说,有要事约诸葛正扬相商,是有关红袖楼的。
诸葛正扬果然应约。
在流水汤汤的风雅亭畔,诸葛正扬远远便看见蓝冲坐在石凳上,背对着自己,他脑子里又跳出红袖楼三个字,想起靳冰越,不由得百感交集。跨上台阶,他便问:"蓝兄,你约我来,所为何事?"蓝冲不动,也没有说话。
诸葛正扬忽然意识到不妥,疾步绕到蓝冲的面前,只见他双眼紧闭,似是睡着了,嘴角还带着猩红的血迹。诸葛正扬面色大变,赶忙解了蓝冲的穴道,扶着他的肩,试图以真气灌入他体内使他苏醒。片刻之后,蓝冲的手指动了动,疲乏地撑开眼睑。他醒了,诸葛正扬却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似有几道混乱的气流游走疯串。
这时,背后传来女子阴冷的笑声。
诸葛正扬趔趄着转过身来。"我知道是你。"他说,"你恨我?你为何始终不肯接受我?"
此时,靳冰越已是红着双目,眼眶含泪。她看看呆滞的蓝冲,又看看满脸痛苦的诸葛正扬,一时心悸,一时心凉。
她说道:"我自知并非你的对手,所以,不得不借用你的这位好朋友。"
刚说完,蓝冲便狠狠地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吼道:"靳冰越,我真是错信你了,你这女子,根本就是凶残毒辣,蛇蝎心肠。你的目标是我,为何要害诸葛兄?"
这愤怒的咆哮,说到最痛处。
靳冰越顿时缄了口。她说不出,说不出自己恨诸葛正扬的原因。说不出那在她看来肮脏污秽如噩梦的往事。但蓝冲其实并不是真的想知道为什么。在他看来靳冰越的报复仅仅是因为诸葛正扬曾经刺瞎了她的眼睛。他不理解,痛恨,因为受到伤害的是他以诚相待的挚友。
诸葛正扬好几次试图站起来,却都是白费力气。他所中的毒,就擦在蓝冲所穿的衣服上,一旦接触,可以使人气血逆行,四肢乏力。靳冰越事前给蓝冲服了解药,所以能保他安然。甚至是他嘴角的那一点血迹,也只是涂抹的鸡血。蓝冲除了吸入过一点迷香,身体各处皆毫发无伤。但诸葛正扬却不知道,他断断续续地哀求着靳冰越:"伤你的人是我,与蓝兄无关,他只是一个铁匠,请你放过他。"
靳冰越眼神一颤,不禁唏嘘。你既然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却为何要做出那样卑劣的行径来?这句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却仿佛是从眼睛里流泻出来。
诸葛正扬看见了,看懂了,他亦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深深地盯着靳冰越那双清澈的眸子。
似是在说,你知道原因的。
是因为痴爱与迷失。
奋不顾身地去做错。
可以在腊月催开菡萏香。可以在盛夏求得潇潇的雨雪。何来章法,何来因果。都只为这人世间的情与爱。
无际无疆。
玉佩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诸葛正扬的坟前。蓝冲抱着酒坛子喝得酩酊大醉,他看见靳冰越款款地走过来,他痴痴笑笑,破口大骂,你,滚。
滚--
靳冰越挑眉道:"在我滚之前,我要你的玉佩给我留做纪念。"
"玉佩?"
蓝冲捏了捏腰间那块通透的白玉,冷笑:"就连我的命你也可以随时拿走,更何况是这破玩意。"说着,一把将玉佩扯下来,对着靳冰越砸过去。玉佩掉进草地里。安然地躺着。靳冰越面无表情,弯腰拾起,突然觉得头顶一阵沁凉。
衣裳全湿了。
满身酒气。
是蓝冲将坛子里的酒全泼在她身上。他指着她哈哈地嘲笑,可是,那笑容却是那么僵硬,带着凄酸,和许多许多的难以言喻。
靳冰越依然沉默着。左手捏着那块玉佩。
右手还托着一个巴掌大的锦盒。
锦盒里,装着一对血淋淋的眼珠子。是诸葛正扬的眼珠子。是靳冰越杀了诸葛正扬以后,当着蓝冲的面挖出来的。
并且,她说,我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之身。
她的表情贪婪又狰狞。
好像她真的是一个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蛇蝎女子。
此刻,她沿着茫茫的山路走远。背后仿佛还充斥着仇恨的目光。她面无表情,打开锦盒将玉佩放进去。她可以回红袖楼交差了。因为雇主为了能证实将来她带回去的眼珠子到底是不是属于蓝冲,要求她同时也带回蓝冲随身的一块玉佩。那玉佩晶莹通透,触感光滑。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就好像抚摸男子昏迷时候熟睡的面颊。
她感到双眼一阵刺痛。视线再度模糊起来。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失明,她的眼睛将恢复得完整无缺,就好像她从来没有到过长风镇,没有遇见过她应该或不应该遇见的人。
可是。
留在心口的疤,是不是也会像某些人那样,成为证据,永远不可抹杀?
这时,她忽然被脚底的树根绊倒了。她仿佛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瞬间向她靠拢,可是,却在某个时刻又静止下来。
她心中一凛。
回过头,除了漆黑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
她没有动,就是那样狼狈地跪地的姿势,仿佛在等待着什么。然而很久很久,周围都只是飘荡着呼呼的风响,和树叶婆娑的凄凉。
是啊,就算看见了,触摸到,又能怎样?还不是四目相对的仇恨与绝望。谁能将这破败的残局挽回。谁能抛开一切,将血淋淋的前事遗忘。谁还能将穿肠的毒当作救命的草。一个眼神,一碗热汤,持续一生的煎熬。
她便缓缓地站起了身,继续前行。
几天之后,她回到红袖楼。心急的雇主早已经守侯在那里。她将锦盒打开,亮出玉佩,雇主拿在手里掂量着,观察了半晌,道:"这个人,并不是我要找的蓝冲。虽然他也吻合那些特征,但这玉佩,却不是我认得的那一块。"
"靳姑娘,你错了。"
雇主的话音刚落,空气突然凝滞,万籁俱寂。然后,靳冰越慢慢地笑开了。那笑声由低沉的凄艾,到放肆的喷薄。
笑得泪花四溅。
笑成一种绝望的哭嚎。
有道是,云雨巫山枉断肠,原来这生生死死的徘徊,不过是笑话一场。
你的每一次点赞,我都认真当成了晚安。
(此处无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