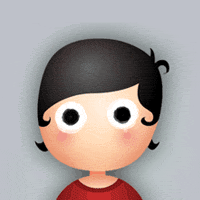请点击上面蓝色的“尹高洁”,每天第一时间订阅尹高洁的文章。也可加我的私人微信:834895029
金庸小说的语言艺术直接秉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延续了“五四”以来文学的现代机素,又适当借鉴了西方文学的技巧,古今中外,熔于一炉,从而形成了金庸独特的文学语言艺术世界,创造了继《红楼梦》以来又一座高峰。金庸小说的语言,文白相间,优美,典雅,洗练,纯熟,如行云流水,春风浩荡,具有非凡的摄取人心的艺术魅力。综观金庸十五部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射雕英雄传》宏阔雄奇,《神雕侠侣》凄美缠绵,《倚天屠龙记》奇幻瑰丽,《天龙八部》深沉悲壮,《笑傲江湖》慷慨豪迈,《鹿鼎记》机智幽默......在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部头林杂之间,中篇《白马啸西风》以其散文诗一般的抒情韵味,如一位玲珑娇小的少女,温柔腼腆,清秀可人,散发着奇异的艺术色彩,让人怜爱,让人赞叹,丝毫不会因为那些伟大之作的傲然屹立而轻视她、忽略她。
《白马啸西风》在语言的叙述艺术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它不同于金庸素往小说庄严、典雅的范式,而更多采取了现代散文诗的抒情的方式,语言雅洁而清淡,忧郁而感伤。正如倪匡所说:“这部小说的妙处,......不在其‘热闹’,而在其‘淡雅’;不在其‘轰动’,而在其‘感伤’;不在其‘曲折’,而在其‘深沉’。”特殊的语言叙述方式营造了意蕴丰富的特殊的美,从而巧妙地传达了小说的主题命意。
细读文本,我们发现这部小说在语言艺术上有三个鲜明的特色,即“三化”(个性化、知识化、民族化),“两美”(感伤美、悲剧美),一性(现代性)。
一、个性化
个性,是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的品格;而个性化的语言,简直就是作品维持持久生命力的保证。从绝大程度上说,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必须由个性化的语言来支撑(构建)。金庸说:“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这里的“个性”,指的是个体的性情与品格,而个体的形象的凸现必须由适合此一“个体”的个性化语言来完成。且看下面这几段:
苏普比她大了两岁,长得很高,站在草地上很有点威武。李文秀道:“你力气很大,是不是?”苏普非常高兴,这小女孩随口一句话,正说中了他最引以为傲的事。他从腰间拔出一柄短刀来,说道:“上个月,我用这把刀砍伤了一头狼,差点儿就砍死了,可惜给逃走了。”
李文秀很是惊奇,道:“你这么厉害?”苏普更加得意了,道:“有两头狼半夜里来咬我家的羊,爹不在家,我便提刀出去赶狼。大狼见了火把便逃了,我一刀砍中了另外一头。”李文秀道:“你砍伤了那头小的?”苏普有些不好意思,点了点头,但随即加上一句:“那大狼倘使不逃走,我就一刀杀了它。”他虽是这么说,自己却实在没有把握。但李文秀深信不疑,道:“恶狼来咬小绵羊,那是该杀的。下次你杀到了狼,来叫我看,好不好?”苏普大喜道:“好啊!等我杀了狼,就剥了狼皮送给你。”李文秀道:“谢谢你啦,那我就给爷爷做一条狼皮垫子。他自己那条已给了我啦。”苏普道:“不!我送给你的,你自己用。你把爷爷的还给他便了。”李文秀点头道:“那也好。”
在两个小小的心灵之中,未来的还没有实现的希望,和过去的事实没有多大分别。他们想到要杀狼,好像那头恶狼真的已经杀死了。
这里,作者用“儿化”的童真笔墨,非常传神地勾画出两个小孩的天真个性:苏普的骄傲豪放,李文秀的温柔仁善。精彩的对白非常贴合两个小孩的年龄与身份。成功地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人物形象,可说是金庸语言艺术上最大的特色。在金庸小说中,人物说的是“自己”的话,而决不会去说别人的话,以至读者根本不必看人物的名字,仅仅通过对话便能猜出说话的人是谁。
二、知识化
金庸的小说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农田水利,经济军事,人情风俗,宗教哲学,文学武功,美食技艺,无所不包,无所不涉,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学人每每惊叹:“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课程来学习研究。”以文化知识含量的博大精深而论,金庸的小说在中国古今作家中毫无愧色地位居第一。
文化知识引入文学作品,决不是花瓶式的摆设,而是作为点染作品的文化背景、烘托情调气氛、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刻画人物性格,甚至以象征、隐喻的形态传递人性内涵与主题命意的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试想一下,如果剥离了那些文化知识,金庸小说是否依然那样具有深厚的“内功”,依然那样大气磅礴、气势恢宏,凛凛然透出巨人风范?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知识是结构金庸全部小说的骨架,骨架散了,肉与灵魂也便失去了依托的主体。
《白马啸西风》是一部只有七、八万字的中篇小说。相对于那些长篇巨制,《白马啸西风》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当然不可能显示出繁复密集的知识意象群。在这里,才大如海的金庸只是随意点染,读者也可从中感受到作者广博的学问。比如:
陈达海说:“你瞧这手帕是丝的,那些山川沙漠的图形,是用棉线织在中间。丝是黄丝,棉线也是黄线,平时瞧不出来,但一染上雪,棉线吸血比丝多,那便分出来了。”
另外还有关于沙漠风暴、洞天景设、民族风俗的描绘,特别是关于古高昌国历史的叙述,《》经典句子的引述,无一不显示了作者的渊博。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知识的引入决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完完全全融入了情节之中,竟是羚羊挂角,好像行文至此便须此,没半分人工矫饰、故意卖弄的痕迹。
三、民族化
在金庸的小说中,民族是一个焦点。
民族间的征战与融合,在金庸小说中有诸多表现,甚至成为一些小说内容的主干。金庸小说涉及的民族有汉、蒙、回、苗、藏、满、哈萨克、契丹、傣、吐蕃、女真......真是天南地北,无所不及,这便极大地拓宽了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使得小说从整体上表现出恢宏阔大的气势。金庸前期小说(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汉族正统观念,随着历史视域的逐步拓宽,中华民族家庭大一统的观念占了上风,这在其后期小说(如《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有着明显的表现,进步的历史观要求作者更好地表现民族间亲密疏离的复杂关系。在《白马啸西风》里,汉人强盗杀害了哈萨克人苏鲁克的妻子与儿子,从此苏鲁克仇视一切汉人,把汉人李文秀也视为“真主降罚的强盗汉人”。后来,当李文秀几次救了苏鲁克一家人,他终于承认:“汉人中有做强盗的汉人,也有李英雄那样的好人(那个假扮老头儿的汉人,不肯在水井中下毒,也该算好人吧?)哈萨克人中有自己那样的好人,也有瓦尔拉齐那样的坏人。”当然,,而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小说语言艺术的民族化。
小说语言艺术的民族化,其实也是语言的个性化,强调的是文学表达的手法和韵味儿。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特色、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性格特征。创作主体的任务,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真实细微地将这些特质很好地表现出来。《白马啸西风》在语言艺术民族化的表现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在李文秀的梦里,爸爸妈妈出现的次数渐渐稀了,她枕头上的泪痕也渐渐少了。她脸上有了更多的笑靥,嘴里有了更多的歌声。当她和苏普一起牧羊的时候,草原上常常飘来了远处青年男女对答的情歌。李文秀觉得这些情致缠绵的歌儿很好听,听得多了,随口便能哼了出来。当然,她还不懂歌里的意义,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对一个女郎这麽颠倒?为什么一个女郎要对一个男人这麽倾心?为什么情人的脚步声使心房剧烈地跳动?为什么窈窕的身子叫人整晚睡不著?只是她清脆地动听地唱了出来。听到的人都说:“这小女孩的歌儿唱得真好,那不像草原上的一只天铃鸟么?”
到了寒冷的冬天,天铃鸟飞到南方温暖的地方去了,但在草地上,李文秀的歌儿仍旧响著:
“啊,亲爱的牧羊少年,
请问你多大年纪?
你半夜里在沙漠独行,
我和你作伴愿不愿意?”
歌声在这里顿了一顿,听到的人心中都在说:“听著这样美丽的歌儿,谁不愿意要你作伴呢?”
跟著歌声又响了起来:
“啊,亲爱的你别生气,
谁好谁坏一时难知。
要戈壁沙漠便为花园,
只须一对好人聚在一起。”
听到歌声的人心底里都开了一朵花,便是最冷酷最荒芜的心底,也升起了温暖:“倘若是一对好人聚在一起,戈壁沙漠自然成了花园,谁又会来生你的气啊?”老年人年轻了二十岁,年轻人心中洋溢欢乐。但唱着情歌的李文秀,却不懂得歌中的意思。
听她歌声最多的,是苏普。他也不懂这些草原上情歌的含意,直到有一天,他们在雪地里遇上了一头恶狼。
浓郁的民族地方风味,活泼率真的民族情歌,朴实的民族心理语言以及疑问排比的抒情句式,交汇融合,创作出优美的绘画意境。
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小说最后一节哈萨克人去请教精通“”最聪明最有学问的老人哈卜拉姆汉人可否与哈萨克人结婚。哈卜拉姆谦恭的话语,背诵的相关章节句子以及哈萨克人对的单纯虔诚的信仰,都使语言的民族化分外显眼,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以上探讨了本小说语言艺术的个性化、知识化与民族化,接着我们来探讨本小说语言艺术在审美层面上的两个特点。
一、感伤美
金庸所有小说中,唯一令笔者潸然泪下的,不是其他的长篇巨制,而是这篇看起来不起眼的《白马啸西风》。
《白马啸西风》在叙事方式上削弱了庄严典雅的成分,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现代的散文诗式的抒情风格。笔调看似漫不经心的,简单的,不加修饰的,其实最是精心结构的。全篇自始至终散发出淡淡的悲哀,淡淡的凄凉,淡淡的忧郁,淡淡的感伤,这使得小说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淡雅感伤的美。
那么,这种淡雅感伤的基调与氛围是如何构建成立的呢?便在一个字:情。
小说叙述了三段情感:一是金银小剑三娘子上官虹与丈夫白马李三、师兄史仲俊之间的爱恨情仇,二是雅丽仙与车尔库、瓦尔拉齐之间的孽海情天,三便是李文秀、苏普、阿曼(其中还夹着“计爷爷”马家骏)之间的爱情。这三段情感具有一个模式:甲爱乙,乙却偏偏爱上了丙,显示了情爱的不可捉摸性与面对不可捉摸的情爱无可奈何的心态。然而,三者在情爱的处理方式上却截然不同:史仲俊在夺宝与抢美的双重心态下,箭杀了李三,上官虹为夫报仇,杀了深爱自己的师兄,最后又剖腹,这一段最是凄艳残酷。瓦尔拉齐因雅丽仙拒绝跟自己私奔,嫉愤之下毒杀了雅丽仙,这正出于一种“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的畸形心理,从毁灭中得到快感。几相比较,第三段情感却纯净得不能再纯净,感伤得不能再感伤:李文秀非但从来没有伤害过苏普与阿曼,还几次搭救了他二人,几次把阿曼安全地送回苏普的怀抱;而马家骏为了救李文秀,更是献出了生命。
“天铃鸟”这一象征意象在小说中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很明显,作者是把它视为温柔、善良、美丽、会唱歌的李文秀的化身的。文中这样叙述李文秀第一次听到天铃鸟歌唱的情景,笔调是清淡的,然而又是凄凉伤感的:
窗外传进来一阵奇妙的宛转的鸟鸣,声音很远,但听得很清楚,又是甜美,又是凄凉,便像一个少女在唱着清脆而柔和的歌。
李文秀侧耳听着,鸣歌之声渐渐远去,终于低微得听不见了。她悲痛的心灵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呆呆的出了一会神,低声道:“爷爷,这鸟儿唱得真好听。”
计老人道:“是的,唱得真好听!那是天铃鸟,鸟儿的歌声像是天上的银铃。这鸟儿只在晚上唱歌,白天睡觉。有人说,这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之后变的。又有些哈萨克人说,这是草原上一个最美丽、最会唱歌的少女死了之后变的。她的情郎不爱她了,她伤心死的。”李文秀迷惘地道:“她最美丽,又最会唱歌,为什么不爱她了?”
计老人出了一会神,长长的叹了口气,说道:“世界上有许多事,你小孩子是不懂的。”这时候,远处草原上的天铃鸟又唱起歌来了。
唱得令人心中又是甜蜜,又是凄凉。
在李文秀心目中,天铃鸟是自由的化身,自由是天铃鸟唯一的财富。她善良的心灵当然不可能容忍自由的丧失,因此,当小苏普用陷阱捉住天铃鸟之后,李文秀便用妈妈留给自己唯一可纪念的玉镯,换来了天铃鸟的自由。天铃鸟在这里,又作为一种媒介,牵起了李文秀与苏普的情缘。
在小说中,天铃鸟作为渲染感伤情调的意象反复出现,它的歌声每响起一次,凄凉的情调便增加一分:
忽然间,远处有一只天铃鸟轻轻的唱起来,唱得那么宛转动听,那么凄凉哀怨。
苏普道:“从前,我常常去捉天铃鸟来玩,玩完之后就弄死了。但那个小女孩很喜欢天铃鸟,送了一只玉镯子给我,叫我放了鸟儿。从此我不再捉了,只听天铃鸟在半夜里唱歌。你们听,唱得多好!”李文秀“嗯”了一声,问道:“那只玉镯子呢,你带在身边么?”苏普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就打碎了,不见了。”
李文秀幽幽的道:“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就打碎了,不见了。”
天铃鸟不断的在唱歌。在寒冷的冬天夜晚,天铃鸟本来不唱歌的,不知道它有什么伤心的事,忍不住要倾吐?
作者不仅仅用象征性的意象“天铃鸟”来渲染情调,还直接反复地用“凄凉”、“哀怨”、“伤心”、“悲伤”、“哭泣”、“眼泪”、“难受”等一系列带有强烈感伤色彩的词语来点染感伤氛围,加强感伤情绪的凝聚力。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的。在小说语言的内部,缓缓流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感意绪,这种悲感意绪源自李文秀温柔、绝望的情爱,而从整体上造成对感情的强烈冲击。作者始终是用诗一样抒情的笔墨在缓缓叙说。当李文秀终于匹马单身告别自己的恋人,行走回归在通往陌生的中原的路上;当一句“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的最后一声长叹,感情的聚集终于达到顶点,从而圆满地完成了感伤美的营造。
二、悲剧美
感伤美是这部小说给予我们初步的审美印象,然而只须稍微深究一下就会发现,小说最终蕴含的是无穷无尽的形而上意义的悲剧美。
古越歌唱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白马啸西风》俨然是这两句歌词的深情演绎。当“木”有了“枝”后,“木”与“山”之间便是一段无法更改的距离。咫尺便是天涯。当彼此的情爱不能融而为一,距离显示的已经不是一种常人所谓的“美”,而是一种精神的孤独。作为个体的人,其实永远是孤独的存在,因为个体往往很难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价值体;价值无法实现,导致的是精神的失落,从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而无法解脱。这是人的悲哀。然而悲哀不止于此。当自身的缺失与别人的拥有形成参照时,自身的缺失便更加不堪一击,从而陷入更深的绝望。小说中有这么一节:
天色渐渐黑了,李文秀坐得远了些。苏普和阿曼手握着手,轻轻说着一些旁人听来毫无意义、但在恋人的耳中心头却是甜蜜无比的情话。火光忽暗忽亮,照着两人的脸。
李文秀坐在火光的圈子之外。
最后一笔简直惊心动魄。在这里,“火光”与“圈子”具有了双关意义:“火光”当然代表爱情、甜蜜、温暖;而“圈子”代表的是界限,是距离,是隔膜,是对外物的自觉排斥。
另外一个重要的象征意象是“坟墓”。“坟墓”代表的是孤独、寒冷,因此也代表渴望、容纳。初读文本的人可能以为李文秀与苏普无法结合的缘由在于李文秀的主动放弃,其实不然,李文秀一直在争取,这通过她一系列的暗示、试探可以看出。那二人无缘的真正根源何在呢?小说中用了“梁祝化蝶”的典故。李文秀说那个“阿秀”早已死了,问苏普道:“要是那坟墓上也裂开了一条大缝,你会不会跳进去?”苏普笑道:“那是故事中说的,不会真的是这样。”李文秀道:“如果那小姑娘很是想念你,你肯跳进去,永远陪她么?”苏普叹了口气道:“不,那个小姑娘只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这一生一世,我是要陪阿曼的。”说着伸出手去,和阿曼双手相握。——原来如此!这样,“火光”、“圈子”与“坟墓”两组意象群鲜明地对峙,这就意味着,无论李文秀怎样爱苏普,她也永远不可能与苏普共构“圈子”,享受“火光”的照耀了,属于她的,只有冷冷的“坟墓”。这就是这段情爱无望而深沉的悲剧所在。
金庸本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人,因此他自觉地赋予几乎每一部小说以悲剧色彩与悲剧意蕴。“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这是金庸切身的生命体验,反映到《白马啸西风》中来,也正是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悲剧美的渊源。
在金庸所有小说中,《白马啸西风》在语言艺术上最具有现代性,这表现在其散文诗式的抒情叙事方式及语言间的自由切换组合上。
承袭了《红楼梦》等优秀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金庸以全知者的姿态,冷静地叙事,本人隐藏在小说背后,绝少站出来干预,一任人物情节的自由发展。金庸大部分小说都是这样,因此使得小说庄严而典雅。而在《白马啸西风》中,特殊的题材内容决定了作者的艺术取向,他采取了主观抒情的方式,几次站出来直抒胸臆。然而作者的直抒胸臆依然是有节制的,不像古龙那样大篇幅的抒情,而是恰到好处,分寸适中,这便加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金庸大部分小说语言间的组合非常严谨,符合中国传统小说的模式。他竭力避免欧化句式。在《白马啸西风》里,这一规范稍微有所打破。正如古龙所说:“在一段长长的句子后面突然以短句截开,就像以刀截断流水,能使语言产生一种奇异的魅力。”这种现代的语言方式在《白马啸西风》里得到显现。其突出的特点是抹去主语。比如:
白马虽然神骏,但不停不息的长途奔跑下来,毕竟累了。何况这时背上乘了三人。白马似乎知道这是主人的生死关头,不用催打,竟自不顾性命的奋力奔跑。
但再奔驰数里,终于渐渐的慢了下来。
计老人出了一会神,长长的叹了口气,说道:“世界上有许多事,你小孩子是不懂的。”这时候,远处草原上的天铃鸟又唱起歌来了。
唱得令人心中又是甜蜜,又是凄凉。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伟大的文学家首先应是杰出的语言大师。语言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建构文学的基础与载体。语言艺术的苍白无力终究无法承载巨大的思想(社会)意识。现当代文学所付出的努力与所得的收获远远不成比例,正在于创作主体把语言艺术与思想(社会)意识相对立,或者说向思想(社会)意识方面的严重倾斜,而或多或少忽视了对语言艺术的关注。
夏志清教授曾谆谆告诫白先勇说:“作家最重要的关怀,不在于题材的选择,而在于表达的手法;一部作品的成功,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这里“表达的手法”、“怎么写”,实际上强调的是“语言艺术”。而现当代大多数作家却恰恰相反,他们关心的是“题材的选择”和“写什么”。
而金庸是超越性的。他既注重“表达的手法”、“怎么写”,又关心“题材的选择”、“写什么”,以其旷世的天才取得了语言艺术与思想(社会)意识之间的高度、完美的结合,成就了他一部部伟大的杰构。金庸把中国语言的文学艺术性推向了极致,他在语言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只有十七世纪的《红楼梦》可堪一比。
2002年4月8-10日
美是什么?
今天看完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胡经之主编),这部教程介绍了许多著名的美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对于“美是什么”这一命题,狄德罗与泰纳提出各自的概念:狄德罗认为,美即关系;而泰纳认为,美即生活。由于这部书不须细读,我仅仅记住了一些常识,所以无法对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展开评述。
对于“美是什么”,我意外地发现,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美是感觉。
对于“美”,我纯粹从形而上的角度看待。
美的存在以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为前提。在人类没有产生以前,一切客观存在都不具有美学意义,孤立于人的主观感受之外的声、色、体(通常作为“美”物化的形态)仅仅只有自身独立的客体价值;而一旦进入主观,进入“心象”的认可,其美学价值方才突现。
客体(包括具体与抽象)在确立自身的美学价值后,其价值的高低异同取决于不同主体的感官直觉、内心体验、情绪流动及心灵感悟。不同的审美主体看待同一客体,因上述因素而观照出不同的审美内涵与审美特征,从而赋予其不同的审美意义。
美在人们不断的生命与内心体验中具有了不同的层次与境界。具象的美属于较低层次,具象的美无须修饰与润色,以本身的固有形态直接进入人的主观世界,娱情悦性,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乐趣。然而正由于它的具象性,使它的审美功能受到局限,这就迫使它借助于内外适应自己的诸多质素,不断膨胀、扩展、甚至消融、弥散,形成一股巨大的张力,突然之间急遽上升,而高度抽象化,便如炙日下的冰水化雾一般。具象美便在这种自我挣扎、分裂的过程中完成了生命的蜕变与升华(而本身的形态并没有改变,或改变多少),从而具有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学内涵。这就是抽象美。这一变化的过程仍然完成于主体的主观世界。抽象美何以比具象美更高一个层次?因为具象美是个别的、具体的,其自身狭隘的形态决定了其影响所及的范围;而抽象美是普遍的、宽泛的,其包容性与覆盖面极其巨大、广阔,也更能给人强烈的审美乐趣。
古往今来无数的哲学家、美学家在苦苦思索、探求美的最高境界,各家各派也都提出了各自独特的观点。在中国古代,老庄的思想最具代表性。老子以辩证法为指导,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认为最美的声音在于无声,最美的形象在于无形,“最美”只能通过人的自我想像来完成,完全把美主观化了。庄子则反对人为,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美的最高境界。“自然”就是“虚无”,主客体都不存在了,这才是最美。老庄的美学思想具有形而上的崇高意义。其实在他们看来,“美即境界”,美与境界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此种思想,千古之下,我辈小子实在惊叹不已。
而在西方,“和谐”是美的最高境界。西方人的空间观念最为强烈,这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形成鲜明对比,正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西方人的建筑性思维决定了他们在审美趣味上的布局倾向:即事物之间的联系都必须符合其内在的规律,顺应这种自在规律的,便是美;反之,违背这种自在规律的,便是丑。这就形成了他们“和谐”的审美取向与审美情趣。“和谐”,意味着“整齐”、“匀称”、不凌乱、不放肆,这从总体上便形成了西方文艺典雅、庄重、静穆、秀丽的文艺风格。西方辉煌富丽的艺术成就证明了“和谐”在美学上的最高价值。
我是一个在思想上具有叛逆性的人,不满足于在前人的思想阴影下苟活徘徊。针对“和谐”之美,我特意提出了“不和谐”之美的概念。一方面,我承认,“和谐美”体现了美的最高价值;但另一方面,我拒绝因为过度推崇“和谐美”而排斥“不和谐美”,我把“不和谐美”也推到与“和谐美”同样的高度,形成双峰并峙之势。这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学思维,两者似互处于二元对立的境地,相互仇视,相互排斥。有人可能会指出,以“不和谐”为美,其实就是以“丑”为美,。这似乎有理。,是在承认“丑”的前提下以其为美的,而“不和谐美”则以“不和谐”本身就是美。所以二者本质不同。其实对于“和谐”与“不和谐”,到底哪一种才是最高的美学,完全要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分析与评判,二者并非完全的对立。在不同的情境下,“和谐”就是“不和谐”,“不和谐”就是“和谐”,由此而实现了二元的转化,从其本身意义上来说,二者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别。高下优劣之别的评判结果,在于不同的人为。
一切美的最高境界的标尺,都是审美主体主观的产物。
然而,一切美都是主观的产物吗?
在坚持美的存在取决于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时,我又无法剥夺美的独立性,这反映了我思想上激烈冲撞的矛盾,这种矛盾有融合解决的可能吗?
美是感觉。因此,美可以包容一切。
2002年4月18日
在此我要对前天提出的“美即感觉”的理论做一些必要的修改与补充。
首先我必须强调美的独立性,审美客体在未进入审美主体的主观世界以前,具有其独立的美学意义,也就是说,审美客体的审美特征与审美内涵脱离审美主体的主观世界时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审美主体的主观世界的消失而同时消失。那么,“美即感觉”这一理念又如何成立呢?
这其实须得从另一视角来考虑。不同的知识修养、文化程度、道德观念、身份立场以及性格特征、人生遭遇、内心体验、情感浓度,决定了不同主体的彼时彼境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情趣。当一个审美客体进入主体的主观世界时,由于上述因素引起主体对客体的审美特征与审美内涵的认识,也就是说,此时此刻,这一客体染上了主体此时此刻的主观审美色彩,于是,这一客体的审美特征与审美内涵得到认知与承认,并极有可能在价值与意义上得到延伸和扩展,或者紧缩与消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取决于感觉,因为感觉的存在而存在,因为感觉的消失而消失。再具体一点说,这种存在/消失仅针对这一个主体,而相对区别于别一个主体——亦即同一种美,在这一个主体消失/存在,而在别一个主体却是存在/消失。
这样,美取决于感觉与美的独立性这一二元对立的矛盾便得到消解。
2002年4月20日
思想随笔
1
冰与火,本来是决然的对立物,一方的存在必然要以另一方的消失或毁灭为前提。然而在余杰的作品里,两者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在对立的同时,两者又相互映衬,相互支撑,任何一方的隐退,都意味着一个整体形象的覆灭。
冷酷与激情,就如冰与火一样,共同构建了我现在的这种性格。我之冷酷,并非天生,是对这变幻莫测的世界表示怀疑,而不由自主以这种方式与之对抗并保护自我。我具激情,则是天生,因为我自由的感情与欲望受不了任何的压抑和束缚。
当我冷酷的时候,别人感觉到我是不可接近的冬天,任何试图接近的企图,都将以其自身寒冷彻骨的感受而迅速瓦解;当我充满激情的时候,话语如万丈瀑布轰轰坠下,如千里黄河滚滚东流,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一股股扑面而来的热浪。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源自同一个孤独的人。正因为孤独,冷酷才得以形成;正因为孤独,激情才是不可缺少的发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独造就了我。
我曾经赞美过孤独,因为孤独给了我力量;我也曾诅咒过孤独,因为孤独让我寂寞。不管“力量”与“寂寞”是如何的紧张与不和谐,现在我只能承认这种生命形态。既然上帝要不断地惩罚我,要不断的锻造我,要我受尽苦难,我也没有办法。
我一生都会在冷酷与激情中行走,因为我永远孤独。
2
我曾经受金庸、倪匡谈话内容的影响,再加之金庸小说传奇性的情节故事的有力支持与证明,我认定:小说唯一的标准是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是什么好小说呢?
现在我否定这一看法。
以前,我带着“好看小说”的阅读习惯去看端川康成、卡夫卡,去看沈从文、郁达夫,结果他们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极度失望。他们的小说情节平淡,语言没有跳跃性,情感没有激情,这严重阻碍了我的阅读速度。他们的小说我几乎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的。读他们的小说我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审美感受,反而在受罪。
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的审美心态已陷入了一个狭窄的胡同。我最喜欢金庸小说,反复地阅读,不由自主以金庸小说的美学标准去衡量别人的小说,这自然会引起对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的自主排斥,这样自身的审美视野就得不到拓展,就无法接受更加缤纷多彩的审美世界。
文学艺术的审美品格多姿多彩,每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具有其独立的审美品格,要想从中感受或领悟其独特的美,就必须用一种包罗万象的审美心态从其独特处切入。审美霸权的确立,将严重阻碍审美效果的获取,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文学艺术,根本不能制定任何审美标准。人的心灵是最自由的,只有以绝对自由的心灵去阅读,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审美愉悦。
3
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分别提出“为人生而艺术(文学)”和“为艺术(文学)而艺术(文学)”的创作口号。“为人生而艺术(文学)”强调文艺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为艺术(文学)而艺术(文学)”则强调文艺独特的审美功能,把文艺的创作当作终极目的,而否定文艺的功利性。纵观现代文学史,其实还有两种类似的观点,,这比“为人生而艺术(文学)”更进一步强调了文艺的功利性。
对以上几种观点我都不苟同,我的口号是:为心灵而艺术(文学)。
文学艺术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审美外观。人有感情、欲望、思想、意志,这些心灵的内在情愫当然不可能总是蛰伏于中,需要膨胀、扩散、外放、升华,然后才能实现生命的运动。“心灵”永久性的雪藏是植物人的标志,而作为运动着的有生命活力的人必须不断释放自己的“心灵”。“心灵”与外在世界的频繁接触,是人“活着”的保证。作为个体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为了获得适合自己的个性特征,而文学艺术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
创作主体决不能单纯为了客观的事物而动笔,而必须是某一客观事物激起了你内在的情愫,使你的“心灵”受到压抑,不释放不足以使“心灵”得到自由,这时候才是动笔的最佳时刻,也只有在这种时刻,创作才能得到完美的发挥。
心灵是不羁的翅膀,自由是它的生命。心灵处于虚化状态时,是最自由的;一旦心灵滞于物,便被束缚了,心灵被束缚,亦即情感、欲望被压抑,思想、意志被桎梏,这时主体就会感到呼吸困难,感到生命在逐渐消退。此时,拯救自己,就成了当务之急。对于创作主体来说,这时,文学艺术就是解放心灵、拯救生命的上帝。
曹雪芹不是为了写《石头记》才写《石头记》,也不是为了警醒世人、促进社会的进步才写《石头记》,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释放自己一生的郁闷。
同样,屈原、李白、苏轼,他们伟大的诗歌,都是心灵世界得以释放的体现。
为心灵而艺术(文学),或者说,为心灵的自由而艺术(文学)。
4
麻木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虚假与真实的混淆而自甘继续麻木,把虚假当真理。我身边的人无一不是这样。他们信奉的是实用主义的处事原则,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当现实压抑个体,远离理想,他们个个愤世嫉俗,表现出青年人激进锋芒的热血情怀;当不合理的现实与自己的利益挂钩,他们便笑着迎合它,承认它。
我自己又何尝没有这样做过?
思想与行为往往难以达成绝对的一致与契合。
人性不能完美,只能正视它,而不能忽视它。
作者简介:
尹高洁,深圳市明日卓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知名自媒体人,其个人博客流量将近800万次。2008年8月从事SEO与软文、文案的实战工作。出版专著:《网络营销从入门到精通》、《淘宝SEO从入门到精通》、《SEO能帮你赚到钱》。
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加我私人微信号交流——
如果你觉得本文对你有价值,有帮助,有启发,请打赏100元。你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