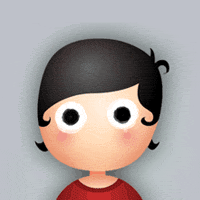核桃
有一天一个女孩给我一个核桃。里面是一张纸条。我看着核桃壳,想起了一些,很久都没有想起过的事。
盛夏,核桃成熟了。其实因为人们的迫不及待,早在大概四月中旬核桃树结出核桃花时,人们就开始品尝核桃的清香了。我还记得对门的邻居刘叔会撩起袖管,三两下便爬上家门口粗壮的核桃树,站在树杈上用脚使劲蹬树枝,天女散花似的掉下来好多核桃花。那是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候之一。核桃花其实并不是花,而是一串根上结满了绿色的穗。刚来北京的我没有见过杨树,以至于把民族大学满地的杨树花认成了核桃花,心中不禁一阵惊喜,仔细辨认后却有一点落寞。那时的我提着塑料口袋,蹲在地上把掉落下来的核桃花一根根捡起,装进袋子。直到塞满整整两大袋,才一脸自豪地满载而归。回到家把核桃花的穗一根根的捋掉,只留下暗绿色的根,水煮之后就可凉拌着吃。因为加了酱油醋,做好后根通常是黑的。几年后我在家乡的餐馆见到饭前凉菜里竟有一盘核桃花,满心欢喜地夹一口放入嘴里。味道无奇,口中却生出一股怪怪的滋味。那时,我突然想到,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绿色的核桃根了。已经有好几年,人们不再摇核桃树,小孩不再捡核桃花。风吹落的核桃花,被汽车的轮胎轧出黑色的汁水,然后被环卫工人扫到马路的一边。
八月中旬,他们用棒子向空中一扔,劈里啪啦掉下好多核桃,摔裂开了它青绿色的外壳。是的,大多数人不知道,核桃和那些年的夏天一样,是绿色的。那时的夏天,没有电脑与空调,阳光慵懒地钻过窗帘,悄悄躺在父亲腿上。那时盛夏的下午是沉睡的时节,而我和父亲却躲在在风扇里贪婪地剥着核桃。那时候的夹壳器还没有捆绑销售,因为那时候的农民也懒得将绿色的外皮刮去,好让人们尝到夏天的新鲜。父亲会用水果刀精准地插入核桃两瓣的缝隙中,轻轻一拧便分为两半。我不管黄绿的新鲜外皮会渗出青墨的汁水,把我的手指染成黑色,只顾把一个个一分为二的核桃捏碎,抠开,剥掉淡黄色的种皮,里面是有的人一辈子也未曾见过的白嫩果肉。
一个下午,我和父亲可以吃完两袋核桃。每年父亲已毕业的学生送来的核桃,总是很快被我们吃光。核桃对父亲和我的吸引力是无穷大的,甚至是在父亲晚上出去喝酒的时候——作为酒鬼的父亲——母亲打电话告诉他家里买了新鲜核桃,他定会推辞掉酒局急匆匆赶回家。即使是母亲骗了他好几次后,他也还是抵不住诱惑。
母亲总是很挑剔,买核桃一定要上了油的,同样也一定不买卡米子——核桃肉卡在壳里不好剥的一类核桃。于是我掌握了一项引以为傲的技能——两下剥光所有的种皮。先把背面面积最大的一片揭下一大片来,再顺着核桃正面的纹路轻轻撕掉沟壑里的皮。第二下从核桃两边开始,顺着脚跟把剩下的全部撕下。也许是为了剥核桃的速度,母亲剥核桃是很草率的。她只是剥掉一大片,剩下不好剥的一点点皮,她会忽略掉。作为全家吃核桃最细致的人,我连一点点皮都不能忍受。那时,母亲剥给我的核桃,我要上下检查好几遍,把残留的皮都剥干净。实在剥不到的,把核桃掰开了也要剥掉。因为我固执的相信,当散发着夏天清香的核桃丢入口中,在唇齿间迸裂,浸散出无限的清脆与圣洁时,容不得一点苦涩。圣洁。核桃是圣洁的。哪怕它的果肉把我的手染黑,一周都洗不掉;哪怕它的种皮嵌进我的指缝,十数天都透着苍黄。但我剥干净所有脏污的外表之后,它的白,它的无暇,是圣洁的。
后来啊,在一个方圆百里见不到一棵核桃树的城市里,我看着惨淡的夕阳余晖,拿着别人送我的核桃,我知道了,原来一个人待太久,会忍不住想起一些东西来的。我意识到,我已经太久没有吃过新鲜核桃了。从何年始,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遗憾的是,我的冬夏,赶上了白雪,却总是错过了核桃的季节。
母亲知道,干核桃我是从来不屑于吃的。小时候试过剥下干核桃枯瘪的皮,可它早已被粘牢,便只好放弃。世界上大多数人为了所谓的“营养”而吞咽那苦涩的黄皮,和早已被染黄的核桃肉,在我看来何其可悲。于是母亲在我离开家乡之后的一个月,焦急地看着核桃成熟上市,然后估摸着等到核桃长势最好的时候,去市场买来十数斤新鲜核桃,分两次提上六楼。坐在凳子上用刀一个个刮掉绿色外皮,弄得满手青黑。然后她把所有核桃洗净,装袋,冻到冰箱最下面的一层。
冬天,归乡。耳机里响着Happy together和California dream,我沉默地望着蜿蜒山路旁的洁白积雪。我的行李箱,一年比一年沉重。回到家,母亲卸下我的行囊,匆忙打开为我新买的火炉,等待一点点暖和起来。母亲脱下围裙,去冰箱最底层拿出已冻霜的核桃,放在火炉边上解冻。然后坐在离我一米远的椅子上,用夹壳器一个个夹开,捏碎,很费力地用指甲抠剥掉皮,一点点地积攒出一大堆泛黄的核桃肉,然后一次性拿给我。
于是,我再也没有在乎过,核桃是否剥的干净。
冰箱很尽力地保住了核桃的新鲜,但失去了清脆。母亲用拙劣的方式,在冬日为我留下了一点盛夏的味道。也许母亲是想念几年前的夏天的,她习惯了孜孜不倦地把自己的手指剥黑,积木般的码出许多白净中带点未剥净的黄皮的核桃,然后分成一多一少的两份,站起,捧在手上,顽皮地塞进父亲嘴里,然后走向我,轻轻放在我的手上。我接过母亲递来的核桃,却失去了与她玩闹的欲望。不知是从那时起或是更早,我剥核桃再也没有那么认真,也再也无法整个下午坐在小板凳上与父亲一起剥到满目疮痍。我咀嚼着不是那么甜的核桃,坐在离他们更远的沙发,但我能看见他们。我想起,在不那么遥远的几年前,这些核桃是会喂到我嘴里的。接着我的脑中浮现出父亲仰在沙发上,我坐在转椅上,母亲在火炉旁解冻核桃的情景。那时候的冬日虽然凛人刺骨,但我想屋子里是不冷的。我感到心里暖暖的,又猛地一酸。
原来,吃核桃带一点苦涩,也未必不可。
现在的我,望着干枯的,小小的,不属于家乡的核桃壳,幻想着有一天我坐在散发着火炉热气的温暖小屋里,像母亲一样亲手为苍颜白鬓的老人和亭亭玉直的女孩剥着核桃,或许还有喃语的垂髫。我用指甲抠下苦涩的核桃皮,这样就不会染秽他们干皱,或柔嫩的手。
而那时的我呢,大概会将不吃核桃皮的原因,连同繁杂时期的惆怅往事,都一同忘了吧。但记忆里弯腰把核桃塞进冰箱的母亲,和青春时的核桃与纸条,我想我会记得。
你好,这儿是听说知了儿
你想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抑或是,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