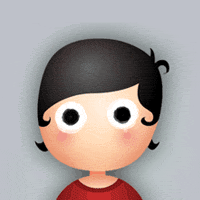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舌头】蓬山纵是万千好,不及儿时膝下欢
“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后我们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
当时在课本上读到这里,一个激灵将我的后背劈的笔直,似乎那个挨打的“太公”是我一样。
龙生九子,各不相同。
爷爷养育了九个子女。父亲是老么,我又是老么家的老么。比例大约就是大伯的长孙要略长我些。小时候,婶娘们看着“小姑”跟在“大侄子”屁股后面下沟上树,都会忍不住逗弄一番。
时至今日,我已经不知道当了几个孩子的“姑奶奶”,应了姑母们挂在嘴上的“人小骨头老”!
辗转一千多公里,五十多个小时,星夜兼程的打个来回。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交通工具:飞机、动车、火车、公交,甚至还有农用小三轮。这也是自我上班以来,第一次因为私事请假。
老公虽然不能理解,但也不离左右的一路相伴。我姥爷去世时,我也不过是痛哭之后拿钱而已。
大伯去了,这对我至亲的人,不是眼泪能解决得了的痛点,生生的生出怨恨来。怨这该拿去蹍成尘沫的老家习俗:嫁出去的闺女不能在家过三十!
因为父亲的顾忌,有家不能回的绝望感,让我在老公的面前歇斯底里了整整一个月。力气抽尽的瞬间,精神不能自持:那可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
大婶们平日里瞧见老公对我的好,贴切的形容他是在养闺女。
我暗自的揣摩过原因:可能是习惯了嬉皮笑脸的我,突然变成一个小水人儿;就像刺猬拔刺一样的鲜血淋漓,唤出了他心底所有的疼惜。
跪在大伯的灵前,心底突然就安宁了。
我的大伯没有死,他只是换了另一个活法。
“大伯,大伯,我要吃西瓜。”徒手破成几瓣。
“大伯,大伯,我要吃野枣。”蹭的一下就去了崖头摘野枣。
“大伯,大伯,马斌不带我玩了。”他轻轻的示意,他们立刻就来拉我。
扬起鞭子赶牛车的沉默汉子,嘴角微微勾起若隐的弧度,倾听着躺在牛车上,望着蓝天的小姑娘信口开合。
当梦里浮现出往昔大伯疼我的情景,醒来眼里总是湿润的。我能清晰的感受到他熟悉的气息充斥着每个角落。
血脉相连。自听说他不能下炕,心里就穿过一丝惶恐,怕他要走了。
他是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啊!如果允许,我相信大伯肯定会活成肆意畅快的大英雄!
我认为整个门族,整个时代都欠我大伯的。
爷爷是地主,听说斗地主的时候,奶奶把金戒指扔在水瓮里都逃脱不了被没收的厄运。
我不知道什么是“成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工分”。但它们所造成的伤害却没有被岁月抹去一丝半痕。
那怕是芝麻大点的权利放到跳梁小丑的手里,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加以滥用,耀武扬威的任意欺压。
最称手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就是“扣帽子”。
头顶上的帽子,压的我们整个家门都低垂着。长兄如父,自己受多少委屈都能咽的下去。
纵然是看着心仪的女人嫁给了贫下中农,也不过是在郁郁中,忍着饥饿继续拼命的挣工分养活大家。
眼下,正是收麦的忙时。大约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麦忙的日子,麦场上晾晒着队里的麦子。一阵急雨突然的从空中倾倒下来,大伯领着稍大点的弟妹赶往麦场,想要抢收麦子。但是,头顶上的“帽子”,将他拦在场外,不准进去。“执法人员”在推搡中将三伯的脑袋磕在旁边的石碾子上,当时就见了红。
怒气上头,大伯单只手将对方狠狠地摔在地上。
自人民公社成立,大伯就在里面拉大锯。大伯是个木匠,黝黑有力的臂膀能让他每天挣十个工分。即使是这样,家里月月年年都欠着队里,张嘴吃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去抢收麦子,无非就是想多挣几分还给队里。
虽然挣工分失败了,但从此再没人敢随意的欺压他的弟妹们。
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默默的将半世的深情,密密匝匝的编织在对弟妹们的疼爱与呵护中。
老四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了,没有蔽体的窝。无数个深夜里,大伯在家里偷偷地做些手工活,一分一厘的攒。好不容易有了一定的数量,竟然被举报了。不仅没收,还得罚款,又欠下了!
他不放弃,又继续在偷偷摸摸中给老四挣出了房钱。
让人一直觉得讽刺的是,他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老四的阔气。
我没有去过那个父亲成天露着大腚、大伯深切痛恨的年代。可是,我却可以理解大伯的不善言语、表情鲜有。只有看见我们儿孙绕膝,他眉宇间才流露出一丝欣喜。
从来没有特意的知会过,他却总能算准我外出的日子以及不定的归期。一步一步从晨光暮色中走来,目光中迎接,目光中远送。
常常,我们爷俩只是在炕上坐一坐,幸福也就盈满无虚了。
突然,我的眼里没了泪。大伯太憋屈了,他只是想换个活法。
我得好好的活着,活成他想要活成的样子!
(摄影:宁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