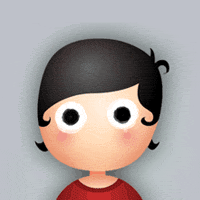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傻子卡布勒》第二曲之浅秋恋歌
卡布勒
傻子
中篇小说
本期字数
12796
阅读时长
25min
第三曲 浅秋恋歌
浅秋的阿克塔斯寒意未显,卡布勒心情低落,转场的一路上也没能跟阿茹詹有什么进展。她和母亲,还有艾别克、叶尔克詹一起被分到管理羊群的工作,羊群又和大部队完全脱节,羊羔们要绕远路走河水缓慢轻浅、宽阔无阻的牧道,只有到晚上,她们才能汇合到大部队一起休息、吃饭。卡布勒非常羡慕自己的小妹叶尔克詹,能时时刻刻、自然随意地陪在阿茹詹身边,小姑娘也非常喜欢崇拜阿茹詹,夜色一降临,疲惫艰辛了一整天,所有人的休闲放松时刻一到,她就在家人面前说起关于她的故事,夸她赶羊时的歌声是多么好听、她处理受惊的马是多么淡定娴熟、她知道怎么只用一片桦树皮做引子快速成功的生一团火、夸她性格恬静温柔,家人们每晚在搭好的简易三角帐篷内喝着茶,静静地听着。在这单调枯燥的天地之间,阿茹詹这样美好的存在,简直就是意外和惊喜。阿克塔斯风大,荒山多,草原到处盘卧着洁白的巨石,比起天堂般的喀楞德,这里令人失望。草皮太薄,游牧人在这里通常只待两个月,便再次迁徙去大地那头更遥远的冬牧场。三家邻居分到的是扎乐帕克套北麓的背风坡,除了天地间突兀的扎乐帕克套,这片牧场可以说是一马平川。水源很少,山沟里只有一两处经常断流的小溪。三家人的毡房呈东西方向带状分布,卡斯木家驻扎在三家人中间,最东边是卡布勒家,和卡斯木大叔家五百米之隔;老人马合詹和妹妹曼尔芙华、侄女阿茹詹驻扎在最西,与卡斯木一家仅几十步之隔,三家的毡房门统一朝西开,因为大多数晴朗的日子里,西面几乎无风。这一片巨石遍布、水源较少的牧场还是有优势的,那就是石头多、建材丰富!卡斯木一家的三个男人,他的大儿子以及雇用的一位诺盖羊倌,再加上卡布勒家的三个劳力,花了一周多时间,用遍布的石块为三家人搭好了结实安全,抗风温暖的羊圈、牛圈。勤劳的哈萨克人在迁居到新的牧场时,自己的毡房搭好不代表转场顺利完成,要帮助所有的牲畜安定下来之后,以牛羊为生的牧人才能完全安下心来。哈萨克人生存的智慧总是展现在细节中,在荒野中与野兽、恶劣的环境为伴,细节能战胜一切。
可是谨慎胆小的牛羊不认识自己的新屋,头两天迟迟不敢入住新房,晃悠在外。牧人对此不急不躁,耐心引导,坚持了两天,牛羊终于肯主动入圈,不需要围追堵截,它们已经深知在寒夜里,羊圈里比外面暖和太多。牛羊的事搞定了,三家人决定热热闹闹地聚在卡布勒家,为每位牧人生涯的又一次壮举喝彩庆祝。为此,卡布勒可是细细准备了一番,他把毡房所有漏风的角落用碎毡片又加固了一层,他取下来挂在壁毯左右两侧的刺绣白布洗了又洗,使之更加雪白;他用木镐把毡房里没被花毡盖住的丑陋的泥土地细细整平,摘除屋内的杂草。母亲为儿子的勤快大悦,总是惊喜地抱住他撒娇,给他的汤饭里多加几块肉,丝毫没看出儿子醉翁之意不在酒。
终于到了大家商定好的日子,卡布勒也在这段时间内积攒了不少勇气。还在这天特意跟弟弟换任务,没去放羊,留在家里帮父亲宰羊待客。秋高气爽,到了下午时分,气温到达一天中最高,旱獭们探头探脑的钻出洞集体晒太阳,马儿们在毡房周围带着马绊子一跳一蹦地吃着草。卡布勒和艾别克从小溪提回来了第八桶水,艾别克和卡布勒形影不离,总是蹭在这家不走,虎头虎脑的惹人怜爱。卡布勒回到家就添柴烧水,艾别克站在门口朝着西面大喊:
“阿茹詹姐姐来咯!”
所有人喜出望外,都纷纷朝门外走去。母亲也停下了手头的针线活,理好头巾后,腿疾发作的她呻吟着起身,出门迎客。大家远远地望着,马合詹老人和阿茹詹一前一后走着,到卡斯木家时,队伍中加入了卡斯木的老婆和儿媳,四个人朝东面缓缓走来,而激动的艾别克已经朝她们跑去,汇合后再一起走过来,小孩子总是天真无邪,从不怕累。木坎和妻子站在前,卡布勒站在父母后面,三个人远远地望着客人,带着笑意长久地望着。阿茹詹戴着精致的女士方顶毡帽,一股黑辫子从帽檐延伸,落在身上,成为了她浅色的朴素衣物最美的装饰。她牵着小艾别克的手,满面春光地朝卡布勒家走来。马合詹老人和木坎、卡布勒一一握手,女宾客们与艾赛慕拥抱、左右行贴面礼问好,卡斯木的大儿媳又向木坎行了屈膝礼。(木坎和卡斯木同属一个部落。)虽然宴请的是每天都能见到的熟人,但也要以最尊重繁复的礼仪迎接,而正式拜访的宾客们也要致以最高敬意。
礼毕,入座。简单地喝过一道茶,获得了马合詹的“巴塔”后,卡布勒和父亲开始宰羊,除了马合詹来人,所有人都作为小辈撤下席面帮着主人家忙前忙后,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当客人。卡斯木的大儿媳阿莱依有着哈萨克女人经典的标志性格,热情开朗、坚强勇敢,已经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她,灵活能干、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弱者,和艾赛慕两人有说有笑地在屋外支好大锅,便回屋开始和面为晚餐做准备了。细心的阿茹詹洗干净茶碗后,一时找不到活干,便拿起艾赛慕绣了一半的毡片,走出毡房,伴着午后爽朗的秋风坐在房前的大石块上绣了起来。不远处和父亲宰羊的卡布勒凝视着她瘦弱的背影,鼓起勇气走进毡房,为她拿了一块羊皮改制的坐垫,忐忑地走到她身后:
“石头上冷,别着凉了。”
阿茹詹回过头,看到他手上的坐垫,又看看他,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和幸福,低下头道了谢,接过坐垫铺好在石块上。卡布勒痴痴地看着她,出了神。阿茹詹见他还定定地站着不走,也不好坐下,站在他对面等着他离开。见他还不走,便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阿茹詹的脸颊已经染上红晕,眼睛里全是清澈见底的少女情愫,她微微抿着嘴巴,脸上羞涩又无措的表情千变万化。痴情的卡布勒心头缠绕着一万句话,这一刻他不想再被恐惧和自卑控制,他要表达,他要说出来,他要让她知道。于是,卡布勒带着无人能及的深情,低声说出了可能是这片牧场几百年来最浪漫的情话:
“第一眼看到你时,我在想,阿拜阿塔的卡浪姆卡斯也不过如此吧!”
话音刚落,小妹叶尔克詹赶牛回来,看到心爱的姐姐,一头钻进了阿茹詹的怀里,大声地向她问好。心慌意乱、手足无措的阿茹詹赶紧就势坐下,背对着卡布勒,没有再回头,紧张地和叶尔克詹胡言乱语地说了些什么。卡布勒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唐突,也羞红了脸。赶紧跑回去继续帮父亲宰羊。
太阳垂在了西面,斜阳从毡房的门照射进来,正在喝茶的人们脸上光彩奕奕,尤其是阿茹詹,暖光打在她的侧脸,五官立体精致,和嫂子对话时深深的眼窝里满是柔情,阿茹詹真是这片牧场所有人心中的美好,话题的中心,美丽纯洁的代表。肉放进了锅里,毡房的炊烟扶摇直上,好像升上了天空和晚霞融为了一体。肉快熟了,在外沐风淋雨辛苦了一天的牧羊人也回来了,卡布勒父子出去迎接、帮忙。放了一天羊,又饿又累的热哈提把马合詹家的十几只羊赶到老人家,数好羊关好圈门,就邀请刚挤完牛奶回来,在家忙了一天的女主人、阿茹詹的母亲曼尔芙华赴宴。曼尔芙华对这位热情阳光的小伙子越来越有好感了。他俩又在半路经过卡斯木一家时,帮他们赶羊系牛,再叫上卡斯木一家子的男人,欢快地往卡布勒家走去。夜幕降临,披星戴月的牧羊人好像忘记了白天的辛劳,为即将到来的放松时刻激动不已,一行人高唱着民歌来到了卡布勒家。
晚宴很愉快,只有卡布勒一人心情复杂。他怕阿茹詹因为自己的冒犯生气了,一直观察她的眼色;而阿茹詹神色凝重,从头到尾没看卡布勒一眼。卡布勒很慌,他觉得自己愚蠢之极,心里七上八下。阿茹詹吃过饭,帮着涮洗碗筷时,卡布勒赶紧上去帮着匀热水,阿茹詹不领情般地走开了。不一会儿,姑娘就称自己不舒服,早早要回去,小妹叶尔克詹和艾别克自告奋勇送她回去了。卡布勒更是心急如焚、六神无主,心里非常懊悔自己的冲动,饿了一天,吃起新鲜的肉却觉得索然无味。
阿克塔斯的天气像孩子的脸,风云突变。在晴朗的上午,乌压压的黑云像卡布勒心底的阴郁那般以压倒性态势突如其来,但一见到阿茹詹,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会烟消云散。距上次尴尬的表白后,阿茹詹似乎在有意躲避卡布勒,即使碰面了也根本不理他。卡布勒为此痛苦得肝肠寸断。这个月里,神游中的卡布勒已经弄丢了近十只羊,爱情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消瘦让他突出的颧骨更明显了,白天他神情呆滞、状态萎靡,还经常在夜里呓语神游。这可吓坏了母亲,硬是卯着劲强迫着卡布勒,和丈夫拉着他去了东边的坑赛阿吾勒,那里住着著名的巴克斯古丽泰,用尽了各种巫术的巴克斯最后只好“诊断”为:小伙子是独自在无人的旷野牧羊时,看到了什么不洁之物,受到了惊吓。
父母听了巴克斯的话吓坏了,一天三顿让他喝肉汤提神,母亲更是命小妹叶尔克詹从木箱底翻出来卡布勒幼时挂在脖子上的“吐玛尔”重新系回脖子上,热哈提负责每夜把驱魔的拜克垫在卡布勒的枕头下。艰辛的游牧生活。每一个人都是家里至关重要的劳动力,每一个人的地位和重要性都是无法替代的,大家迫切希望卡布勒能快点好起来,家庭劳作能步入正轨。卡布勒的病情惊动了整个阿克塔斯的几十家人,成为了牧人放羊时重要的议题,他们口口相传着卡布勒的病情,恐惧被放大,病情被夸张,那个秋天,几乎所有牧人都约定着成双结对去放羊。远近的哈萨克人都带着礼物,跨越几座山、几条河探望生病的卡布勒。每一个长者看望过卡布勒,在他家用过餐后,都会为正在受着苦难的人真诚地给出自己最真心的“巴塔”,然后对木坎夫妇致以最暖心的问候和同情,献上自己的礼物,有时是一剂偏方,有时是一肚子酥油,总之都是慰问者最真实的一片心意,然后告辞,策马消失在茫茫荒野中。
卡布勒漠然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觉得一切都很可笑,什么都不想解释,一句话也不想说。对前来探望的朋友提出的如“你看到的萨义丹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被攻击”等种种愚蠢问题诸感到恼羞成怒。他得不到阿茹詹的确切答案,但她的态度又是那么明显。阿茹詹就在离自己不到五百米的地方呼吸着、劳动着、绽放着,却明明比她在占布尔勒时还遥远。卡布勒成天就那么无力的躺在毡房左侧的角落里,躺在那里默默地感受着她,脑子里绝望地回忆一切,耳朵里听着家人说起她的名字、她家的事,眼睛里流着旁人无法理解的泪水。他失色的人生好不容易有了颜色,他静如死水的命运里好不容易有了一点波澜,他空白单调的感情里好不容易有了强烈激荡,一切都将幻灭了。他单方面的臆想终究要面对现实的残酷。在某个与世隔绝的下午,卡布勒躺在那里睡了又醒,父亲和热哈提放牧去了,母亲坐在花毡边上做着针线活喃喃地自言自语,妹妹叶尔克詹烧水砍柴,扫地洗衣,听得卡布勒又愧疚又无力。他感受到一行人正从东边策马奔来,妈妈和叶尔克詹走出门眺望,来人还带着狗,想必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片刻后就听到母亲开始呜咽,对方中有一位女人也放声地哭了起来,两人相拥而泣。卡布勒侧耳一听,来人正是自己早早出嫁的妹妹巴丽根,来探病的肯定还有妹夫一家,心中无名火四起。
一行人见过面行过礼后,热热闹闹地进了毡房,又神色凝重地来到卡布勒床前慰问,卡布勒面无表情地向妹妹和妹夫,还有长辈亲家们问了好,寒暄着跟他们喝了一道茶后,便觉得索然无味,披上外套出了门去。眼前的阿克塔斯又荒凉了不少,他觉得自己的上衣宽大了许多,秋风无情地钻进衣物,他紧了紧外套,朝扎乐帕克套山脚下的巨石走去。每走一步,他都觉得双腿发软,耳旁的风好像也在嘲笑他,这片草原上的所有男人,包括父亲、恩师侯赛因、终身未娶的马合詹老人,他们一定也经历过这番爱情的苦涩,唯独自己像个弱者一样被打败了,就像童年时次次被打败在摔跤场,自己一定是最病态的无斗志的弱者,卡布勒觉得自己活像天地间的一个笑话。他不知道这场闹剧该如何收场,更不知道自己的痛苦会在哪一天结束,他逃避着现实生活,而阿茹詹更像受了惊的小鹿般逃避着他。终于走到了巨石,虚弱的卡布勒一屁股坐上去,气喘吁吁。从衣服里掏出来诗集,想求助书籍找到解脱的办法。想象力在诗歌中是桥梁,在爱情中却是迷雾重重的森林,卡布勒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困在其中。
“卡布勒哥,”阿茹詹朦胧动听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卡布勒像被闪电击中了似的猛回过头,在巨石后面,瘦弱的阿茹詹提着水,站在不远处定定地仰视着他。她放下水桶,轻盈地绕到巨石前,站到了卡布勒的正前方,脸上没有腼腆的笑容,眉头紧蹙。卡布勒看着她明月般的眼睛,心开始绞痛起来,默默地等待着她的发言,周围一切都静下来,风停树静,连巴丽根家跟来一直狂吠的狗也都在这一刻静了下来。全世界都在等着阿茹詹的答复。
“听说您生病了,我希望您早日好起来。至于您上次说的话,我想您一定是糊涂了,您是读过书的文化人,我只是穷人家的穷姑娘,而我心里也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勇士。”
阿茹詹一板一眼、流利快速地说完了这段话,眼神坚定、不怒自威,一定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练习了很久的措辞。没等卡布勒的回应,阿茹詹轻快地走了,她的拒绝带着孩子气的直接,她的眼神中没有一丝犹豫。卡布勒无力地坐在巨石上,深深地看着她的背影,脑子空白心里却有一颗石头重重砸下来,尘埃落定,“勇士”一词深深地刺激着他敏感的神经。他已经深深相信了有这样一位勇士的存在,就在阿茹詹的明眸里,扎着像落叶松那样深远的根,盘踞在她天真无邪的内心里。
巴丽根一行人在父母家呆了半周,三家人轮流请他们做客,卡布勒一次也没有参与。他好像长在了毡房边缘的被窝里,所有人都热情洋溢,秋日的暖阳却一次也没有照射进他黯淡的内心。热哈提倒是很高兴,一周后就是他期待已久的婚礼了,他每天都在努力驯马,求着妈妈染制颜色鲜艳的羊毛绳为自己的走马束发装扮。三家人都要去参加那场婚礼,艾赛慕决定一家人为新人制作一块新花毡作为贺礼送去,卡斯木家马上决定他们做壁毯,而人口单薄的阿茹詹家就不能做耗费人力的大件礼品了,但还是决定绣一组枕套和被套送给即将大婚的新人。除了卡布勒,所有人都在忙碌中赶工。深秋,整个牧场为一场婚礼沸腾。
阿克塔斯牧场十天来异常忙碌,秋季本不是适合制作花毡的季节,风大雨多,晒制羊毛的天气条件不好。但婚礼将至,大家只好硬着头皮赶制贺礼。妇女们趁着天晴无风时赶紧剪羊毛,洗羊毛、晒羊毛,又花上一整天功夫弹打,使羊毛膨化松软,卡布勒一家便开始擀毡片,在芨芨草席上整齐铺满羊毛,卷起来扎紧后,加上巴丽根一家人总共十个人来回踢打席卷,从卡布勒家一直踢到卡斯木家,这拨人休息,在卡斯木家喝上一道茶;换一拨人上阵踢回来,期间艾别克用开水不断浇灌席卷好让里面的羊毛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踢几米远就停下来,所有人倒在席卷上用肘部不断猛击,然后再继续踢.....总之非常费劲地制好了毡片,然后女人们开始细细地绣制花毡,染成红色的羊角纹形状的毡条搭配染成绿色的粗羊毛线,针脚错落有致地缝在大毡片上,哈萨克女人们多么会驾驭色彩啊!这些稀有的染料,可是艾赛慕再三嘱咐木坎去县里逛巴扎时用两头羊换的,虽然昂贵,但哈萨克人绝对不会吝惜美化生活环境的成本。不到两天,一条浓墨重彩、精致美丽的花毡制成了,所有人都长久地凝视着艳丽精致的作品,想象着新婚的新人收到这块花毡时的幸福表情。没有一个人抱怨劳动的艰辛,大家乐在其中。闭塞的草原,有钱也没不到想要的东西,所有的生活用品、装饰品都由牧人真心付出的劳动和智慧换取,因此,每个人都依靠草原充实而有价值地、纯粹地活着。
热哈提以自己要参加赛马为由没有参加劳动,他几乎每天都给他的走马换一个发型,宝贝的不得了。卡布勒看起来也没有起初那般痛苦的样子了,出于愧疚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无限地躺着和软弱下去了。他每天早早出发就去放羊,走得远远的,去一个不可能碰到阿茹詹的草场,在大地之间寻找慰藉,茫茫的草原上的一草一木向他给予温柔,他在漫长地孤独中治愈自己的失恋,在无人的荒野宣泄着自己的疯狂,吼叫、痛哭,向山羊诉说自己失败的人生。父母把他的这种变化理解为痊愈,非常高兴,向所有来家里做客的牧人夸张地宣传着巴克斯的医术是多么的高明。
婚礼两天后在五座山之外的托尔盖阿吾勒举行。大家密切跟进婚礼的新动态,向每一个路过的牧人打听最新消息,所有人满怀期待。卡布勒坚持不去这场婚礼,因为他知道阿茹詹一定会去。但被母亲强迫着拉上了路,艾赛慕认为卡布勒性格孤僻就是因为总是逃避与人交流的场合而渐渐变得不善言谈,一听他不去几乎是绑着他带上了路。全家人穿戴整齐,十二岁的小妹叶尔克詹穿着母亲新做的枣红色长裙,卷发修饰着可爱的脸型,脖子、耳朵上带着蓝锆石首饰,固定在发尾的三角形发饰闪闪发光,没想到自己的小妹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她含情脉脉的月牙眼已经很有几分成熟女性的味道,浅笑时露出的虎牙又是另一幅小姑娘的神态,花一般的年纪,绽放在草原上,每天与粗活、累活为伴却一点也没有影响哈萨克姑娘们的美貌,遇到正式场合该鲜亮时,一个个都是沉鱼落雁的美女。一大早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出发了,母亲艾赛慕的马上还载着贺礼,一大卷花毡被固定在身后,神气极了,比她神气的还有热哈提,皮靴崭新,塔克牙上还有一大簇“乌克”修饰,马更是被装饰得五彩缤纷!一家子到达卡斯木家的毡房时,他们一家也策马加入了大部队,同样也各个光鲜亮丽,儿媳阿莱依挺着大肚子不方便就留下看家了,艾别克最兴奋,跑在所有人前头,策马奔向阿茹詹家,大声呼喊:
“阿茹詹姐姐!我们出发咯!”
阿茹詹一出场又成为了大家的焦点,明亮得就像毡房里的那盏马灯。她穿着浅蓝色的绒面长裙,裙面上全是自己绣的精致纹饰,头发因抹了马油而显得亮丽顺滑,利索地辫成了一股,红宝石的耳坠显得她的脖子欣长白洁。阿茹詹家的灰马也载着厚重的贺礼。就这样,越走队伍越壮大,经过每一个山口,都不断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游牧人加入了赴宴大队。一路上阿茹詹紧紧跟在母亲的马后,卡布勒拖沓地跟在队伍的最后,一声不吭,遥遥地看着她的背影。中午时分,众人翻越过第五座山,山脚的一块平原上热闹非凡,人马集聚,其中的一顶雪白的毡房崭新高挺,一看就是婚房。婚房的不远处便是哈萨克人巨大的“爱情秋千”,被装饰得五彩缤纷,所有的小辈都聚在那里荡秋千,传出阵阵欢笑和惊叫。几座毡房周围铺着花毡,屋内坐不下的客人们围坐一圈,伴着秋风喝茶吃肉,真是一片祥和。前来迎接的小伙子大声打着招呼请大部队下山。
婚礼主人忙里忙外,卡布勒一行人系马,卸下贺礼送给婚礼的主人,问好道喜,男客和女宾被引向不同的毡房。“揭面纱”仪式已经结束了,尽管他们出门很早了,但还是没赶上,小艾别克为此很不高兴,溜到婚房偷偷看了一眼新娘子,新娘子带着“萨乌克烈”高帽,全身华丽鲜亮,可真漂亮啊!这是一家牛羊满坡、驼马遍地的富人家,大儿子娶妻当然要隆重正式。人们吃饭的席间,还请来了当地著名的阿肯和“铁尔麦”演唱能手为大家助兴,赛马的头等奖也是草原中稀少昂贵的牦牛。大人们在婚礼上遇到了久违的喀楞德的其他老乡,更是高兴得不行。大家吃着美食,观赏者着表演,好惬意!赛马者都到齐后,主持婚礼的长者宣布赛马比赛即将开始,于是所有人骑上马,浩浩荡荡往东边的平原走去。赛马的场地是一块四周高中间地的洼地,似乎是重复利用了多年的宽阔场地,没有草皮,大地的肌肤裸露出来,小骑手们神气地骑着赛马进入场地,赛马的主人也紧跟在后,观赛者在四周的高坡上散坐着。男人们开始下赌注,女人们则在讨论谁家的马装饰得有新意,老奶奶们也蹒跚着赶来了,因为小骑手中有自己的小孙子,她们要一睹心肝宝贝的飒爽英姿。卡布勒坐在父亲身边,四处询问有没有谁知道自己的恩师侯赛因的近况,热闹的婚礼化解了一部分心头的哀怨,他也万分期待着热哈提的宝马登场。阿茹詹则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美丽动人的她们围坐在一堆,像极了山间聚簇的花丛。
比赛开始了,阵阵马蹄迅速激起黄沙一片,小骑手们各个有模有样掌控着马,小小的身躯扒在马上,大声发布着号令,在大家的惊呼中,一圈顺利结束,还有九圈,群马奔腾,场面壮观至极,围观的所有哈萨克人按耐不住血液里涌上来的激情,全都站起来了,大声为自己阿吾勒的赛马呐喊助威。每一匹骏马都毫不示弱,展现自己最矫健的身姿和肌肉,疯狂地奔跑着,第三圈快结束了,弯道时一个瘦弱的小骑手没能拉住缰绳,没能转过弯去,于是马直直地冲上山坡奔向人群,偏离了赛道,看着失控的马谁都不害怕,都在尽力帮小孩子,马的主人一家子在叹息,错失了良机,可是小骑手不在意输赢,控制住马后又立即策马奔回赛道,坚持完成比赛,小小的身影倔强又勇敢,看客们都致以掌声,所有人热血沸腾。已经进入第十圈了,目前热哈提的白额黑马和一匹枣红马半米之遥,正在进行着最后的拼搏,此时才进入第九圈的一个小骑手坠马了,惊得奶奶们“哦咿拜”“哦咿拜”地大声尖叫,焦虑地询问是谁家的孩子,赛场边上的男人们赶紧上前帮助,却差点被其他的走马,这场小混乱干扰了排在第一的枣红马,在最后时机,热哈提的白额黑马后来居上,获得了第一!周围人陷入狂欢,父母都激动地呐喊起来,冲下山去抱住自己的儿子,热哈提激动地又跳又叫,所有人都拥上前来道贺,他被团团围住,热哈提赶紧接下来马上的小骑手,把他扛在肩上,左手牵着战马,威风十足,出尽了风头!
接下来的时间里,热哈提简直成为了整场婚礼的焦点,他又参加了摔跤,虽然没得冠,大家也致以热烈的掌声,比冠军有风头,他站在那里热情阳光地笑着,几乎所有托尔该的姑娘都在远远的观望着这位魁梧高大的大男孩。母亲无比自豪,非常谦虚地接受者女伴们的夸赞。卡布勒也为弟弟感到高兴,他总是那么阳光快乐,所以幸运之神频频眷顾他。直到“捡银子”比赛时,自家的马夺了头奖的卡布勒的心情都很不错,但是,当他看到热哈提把策马奔驰弯腰捡到的银戒指转手便送给了场边光彩照人的阿茹詹时,嫉妒的岩浆从心底翻滚上来,怒火中烧的卡布勒突然想起来阿茹詹的那位神秘“勇士”,脑子一片空白的他似乎终于明白了阿茹詹对自己态度那么决绝的原因。
整个婚礼是在强烈的嫉妒中度过的,当热哈提邀请阿茹詹玩“爱情秋千”,两个人在秋千上眉目传情时,卡布勒心中更加笃定了,无法在这种喜庆的场合再多待一秒。不顾母亲的阻挠,立即打马回家。路上下起了大雨,在狂风暴雨中卡布勒策马狂奔,他脆弱的神经被脑海中刺眼的那幕情景残忍地蹂躏,几个月来对阿茹詹的美好向往瞬间幻灭,他觉得自己像极了古尔邦节时等待牺牲的那只羊,再怎么挣扎也会被命运围追堵截,与热哈提的光辉比起来,自己那次文绉绉的表白简直像个笑话。最可恨的是,他连对阿茹詹和热哈提怨恨的勇气都没有,他怨恨不起来,只恨自己活得多余。泪水与雨水掺杂在一起,他的马在昏暗的天色中发出阵阵不安的嘶鸣,好像也在陪他一起痛哭。此时的卡布勒只有一个想法:基于十八年来遭遇的一切,他不出生最好,其次是尽快地死去。但死亡看起来像长长的小山,一列山脉,他每天骑马向前,却从未抵达。他很难解释自己性格的成因,但卡布勒明确知道,如果是热哈提面对着像自己一样的糟糕人生,以他乐观向上的性格一定能用尽办法让生命精彩起来,可偏偏,性格不好的人同时也不走运,他对自己生命的厌烦此刻达到了极致。回到家后身心俱疲、淋了三小时暴雨的卡布勒卧床不起,额头的温度令人惧怕,发着高烧的他说起了胡话,但坚决不同意父母再带他去神医古丽泰那里看病的提议,他不想像上次那般出丑。迷迷糊糊的他烧了三天三夜,他的牧羊犬在毡房门口忧心忡忡地观望。在一个秋意萧瑟的下午他独自醒来,恍若隔世,看着天窗的缝隙投射下的一束光出了神,他多么希望自己混沌的人生也能出现这样一条光明的缝隙。
就像卡斯木第一眼爱上了阿茹詹一样,阿茹詹在阳光帅气笑起来有虎牙的热哈提接过她手中驼奶时的那一刻就深深地被他吸引了,每日听着他以洪亮的声音唱着民歌帮着把家里的羊赶回家,好感徒增;善良外向的大男孩赛马摔跤样样在行,魁梧强壮的他帮着搭好的毡房又高又结实,每次上马前都极为绅士地为自己调整马镫的高度、马肚带的松紧;热哈提说话是那么幽默风趣,能让严肃的母亲都开怀大笑。这么优秀的热哈提,当然是所有阿茹心中的梦想。情窦初开的阿茹詹沉浸在自己青涩的暗恋中,所以当她突然遭到卡布勒唐突的告白时,才意识到平日里孤言寡语的这位男人的存在,他不仅真实地存在着,居然还爱慕着自己,虽然阿茹詹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但当时阿茹詹的内心清晰地回响着一个名字“热哈提”,因此初次被告白的小鹿乱撞的阿茹詹心中的欣喜和快乐迅速恶化为对卡布勒的无端厌恶,她知道这绝对是一段互相矛盾的感情,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卡布勒的一片痴心。
秋去冬来,阿克塔斯牧场变得和卡布勒的内心一样荒芜,哈萨克人再一次启程,过程同样的繁琐艰难,在迁徙中续写着自己的游牧生涯。在贫瘠的冬牧场,生活将更为艰难寒冷,也许会有可怕的雪灾,长冬慢慢,热哈提无比怀念温暖富足的夏牧场时光。就在大家启程之际,侯赛因先生的侄女唐努尔赶到了阿克塔斯,原本被托付给卡斯木大叔一家的孤女唐努尔,因为不放心年长的叔叔孤身一人前往遥远的奥木卜,勇敢的唐努尔把老人送到奥木卜,又帮他在市里安定下来才折回来的。唐努尔的到来给这片牧场带来了太多新鲜事,首先,她从市里给愿意收留自己还帮自家代牧的卡斯木大叔带回来一块昂贵的怀表,表达自己最真挚的谢意。可以说,秋牧场的全体哈萨克人都被这块制作精细的怀表震惊了,所有男人都专程到卡斯木家欣赏这块只有奶疙瘩大小、却能精确记录时间的仪器。唐努尔一起带回来的,还有侯赛因给自己的得意门生卡布勒寄来的信。信中透露了太多在闭塞的草原接收不到的外界讯息:原来,在哈萨克人还沉溺于内讧时,,第一次工业革命都已经接近尾声,封建的帝国主义沙皇的地位目前岌岌可危,伟大的者正积蓄雄厚力量,,光明即将降临在饱受压榨的人民身上。在信中,恩师带来的新讯息极大地鼓舞了卡布勒,他绝心离开这片令他压抑愤怒的牧场,离开万年不变的游牧生活,勇敢地加入瞬息万变的外界,决定为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向冬牧场前进的路,花费了牧人六天之久,冻死了一只先天瘦弱的羔羊,第三天深夜里突袭转场大队的饿急眼的狼群咬死了一只半大的牛犊,可惜是头能繁衍后代的母牛。还有一件有关生死的大事,就是卡斯木大叔的大儿媳阿莱依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柔软粉嫩的女婴在艰难寒冷的转场途中降生,母女平安,产后的母亲坚强无比,似乎产褥热这样的产后病绝对不会发生在她这样钢铁般的哈萨克女人身上。新生命的降生鼓舞了每一个因寒冷和劳累而麻木了的游牧人,她是一个女孩子啊,象征着希望和族群的未来,她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生命,马合詹阿塔通过命名仪式赐予她美名“巴彦”,希望她能成为家族幸福的延续。“巴彦”像天赐的那般,降生在了驼队,一出生就在驼峰间的摇篮里摇摇晃晃地开始了游牧人生,新的生命安抚了这一些被猛兽攻击后焦虑不安的牧人,他们平安赶到了冬牧场科思套。这场迁徙之后,所有牧人都忘记了舟车劳顿中的种种不适和困难,只记得小孩子诞生的那个美妙的傍晚,似乎所有人在那一刻重获新生。
科思套的一片山间小盆地是卡布勒一行人理想的冬季驻扎点,三家人商量好把前人留下的一间破旧却完整的小木屋让给马合詹老人一家住,卡布勒和卡斯木一家挖好了冬窝子,安定下来后,马合詹老人邀请大家伙儿来家里吃肉以表谢意,带着淳朴的期待做了最鼓舞人心的“巴塔”,牧人没有过多的贪念,只希望严厉的冬天不会给他们带来雪灾和旱灾,没有意外和离别,只求平安过冬。席上热情的阿莱依大嫂态度暧昧地有意开起热哈提和阿茹詹的玩笑来,两个年轻人都羞红了脸,辛亏卡布勒没有来做客碰见这糟心的一幕。从阿克塔斯临出发前,热哈提已经在一次早茶时一本正经地向家里坦白了自己的感情,当然卡布勒也在场,他装作若无其事似的大方快乐地祝福了弟弟,并故作镇定地表示关于婚期,还没有心仪对象的自己会让步。母亲高兴极了,如大山般沉默的父亲也露出了难得的欣喜情绪,接下来的流程所有人心知肚明,卡布勒更是明白。这增添了他想离开的决心,他一遍遍读着侯赛因捎给他的信坚定着内心,他想逃离这里,更想摆脱自己尴尬痛苦的处境。卡布勒经历了只有他和阿茹詹知道的一场无声的战争,没有具体的决斗对象,也许有,但绝对不是弟弟热哈提,结局输得很惨,像此前人生中的每一次败北那样惨烈。卡布勒突然明白了邂逅阿茹詹的那一天,梦中的祖父口中令人不解的那句“你要输了,孩子。”的具体含义。
草皮越来越薄,可怜的牛羊成天饿肚子,满怀期待地用蹄子扒开雪却屡屡空腹而归。温带荒漠地带的冬牧场,没有直接的水源,只靠积雪度日的哈萨克人在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辽阔大地间勇敢无畏地活着,卡布勒打算帮家里熬过这个冬天,迁至春牧场时就离开。女中豪杰唐努尔能在冰天雪地独自放牧,运气好时,弓马娴熟的她还能打回来皮毛完整的红狐,等碰到俄罗斯皮毛贩子路过牧场时就能卖个好价钱,叔叔一人在城市的开销都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姑娘以这种方式在资助。唐努尔性格刚烈,做事稳妥,在卡斯木家完全能充当一个男性劳动力,游牧生活已经把孤女锻造成了英雄,她只有在卡布勒面前才会流露罕见的温柔,卡布勒却看不到她可爱的温柔一面。作为知己,他把自己想去奥木卜市投奔侯赛因先生的想法告诉了她,她连连摇头否定了卡布勒的冒险精神。唐努尔在奥木卜市目睹了封建军阀的残暴和不择手段,她深谙目前的局势混乱,叔叔的反抗不堪一击,他们建立起的所谓的哈萨克知识分子联盟也一触即溃。
果不其然,在一个狂风大作的阴暗傍晚,西面的黑山上奔来一位行色匆忙的男人,路过卡布勒家时没有问好行礼直冲卡斯木家奔去了,卡布勒看见他厚重的衣物被雾气彻底的打湿,马鬃及男子只露出的眉毛眼睛全部染上了白霜,一定是在寒冬里骑了一整天马才赶到这里。男子在卡斯木家门口勒马站定,走进地窝子不久后,卡斯木家传出了唐努尔惊天动地的哀嚎声,卡布勒立即明白了,那位男子是报丧人。全家人立即扔下手头的活奔向卡斯木家。
侯赛因先生在奥木卜市遭到了暗杀,杀手的身份不言而喻,努尔兰伯勒斯指着有伤口的尸体坚称侯赛因先生是不幸坠马身亡,一派胡言地草草了事。可笑的是,同侯赛因先生一同“坠马身亡”的,还有多位其他阿吾勒的锲贤。悲愤的情绪蔓延在冬季,人们的怒火好像要融化掉茫茫大地上几尺厚的积雪。德高望重的侯赛因先生的葬礼在大雪中进行,所有喀楞德的牧人都不远千里来与这位可敬的学者告别。一个老人辞世了,就好像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了。卡布勒心如刀割,无法接受自己的恩师惨遭虐杀的现实,更无从安慰悲痛万分的唐努尔,孤女那痛彻心扉的挽歌回荡在荒芜冰冷的冬牧场:
“我的父亲没有了,百灵不再欢唱了,
山鹰从树上飞走了,飞上天空不回归了,
父亲心胸辽阔,志在崇山峻岭,
我们登上峰顶,却看不见他的足迹,
死神把雄鹰带走了,
可雏鹰翅膀还没有长硬啊,
离开父亲怎能飞翔啊!
家里那匹高大的黑驼上了高山,
没了父亲下不来了!
父亲走了,他的猎鹰孤独了
女儿心中的灯塔啊,就这样坍塌了。”
就这样,哈萨克人不久前用婉转动听的“齐力迭哈纳”把小婴儿巴彦迎到了这个世界,就又用悲痛不绝的“卓和套”挽歌把侯赛因老人送走了。哈萨克谚语“歌声打开你的生命之门,歌声又送你进入坟墓”真耐人寻味。
哈萨克人没有料到,这场“谋杀”只是沙皇胡作非为的开端,接下来无能的官僚造成的混乱更令人可怕,沙皇对人民要求和平自由的呼声置之不理。此前,昏庸自大的沙皇在德国前线组织的进攻招致了巨大伤亡,人民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引起万恶的封建帝国主义的同情,他们反倒更变本加厉地将魔爪伸向了哈萨克草原。沙皇尼古拉二世大笔一挥,一纸军令便征走了成千上万的哈萨克男人,而每一个都是各个家庭游牧生活得以维续的劳动力和顶梁柱。卡布勒万万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种被迫的方式离开这片令他痛苦悲伤的故土,那一年是1916年,卡布勒刚满十八岁,不久后在某场战役中手无寸铁地被敌军残忍杀害,永远的死在了异乡。他再也回不去富饶美丽的喀楞德,静谧安宁的阿克塔斯,寒冷艰苦的科思套,苦涩的命运连玩笑都不会再给他开一个了。那片白桦林能不能一直保守着他的秘密,刻着字的马鞭不知丢在了哪里,跟自己误会重重的母亲能否释怀,幸运的热哈提是否依旧吉人天相,带着所有的问题,卡布勒痛苦纠结、短暂孤独的人生被强制停止。最后一刻,所有的痛苦都消散了,卡布勒回到了那个慵懒的下午,这一次他勇敢地与问路的阿茹詹结识。
作者简介:
热依扎,写作、摄影爱好者。1994年出生于新疆博乐,曾任多个平台小编,于2017年11月开创个人平台Buyrabas。
-End-
感谢阅读
特别说明
《傻子卡布勒》中篇小说是本平台小编热依扎原创文字,因前期第一次发布时平台还不能加原创功能,现为保护版权,重新标注发布,望各位朋友理解。
Buyrabas
小众的Buyrabas 想邂逅特别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