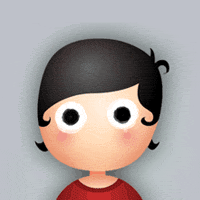春天剜菜指南,田野里那些最可口的草儿 豫记
骆淑景 | 文
小时候,正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养兔、养猪却没有人管。然而养猪,得喂一年才有收入。
养兔就不同了。平均两个月剪一次兔毛,拿到土产公司换几块钱,最多时卖过二十多块,解决家里的点灯用油、吃盐、学生作业本等问题。于是家家都养兔子,我家最多时养过20多只。
这样放学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提上篮子去割草。
割草,我们不叫“割”,也不叫“剜”,我们叫“拽”,就是用手。事实上,草旺盛的时候,用镰刀是割,草才露个尖尖芽时,拿着铲刀应该叫剜才对,但我们一律叫拽。
面条菜
麦田里最多的是面条菜、麦秸籽、羊蹄甲,还有一种“米米蒿”。面条菜和麦秸籽长得象,只是一瘦一胖罢了。
城里来的孩子老分不清,而我们,一眼就知道哪是面条菜哪是麦秸籽。面条菜可以“下锅”,煮面条或者熬糁子汤时,锅里放一些,饭就好吃很多。
菜地里长得最多的是荠荠菜,还有蚂蚱菜,学名叫马齿苋。荠荠菜用滚水烫了,和鸡蛋炒了,包菜饺子,再没有恁好吃了。蚂蚱菜蒸馍,虚虚的,可好吃了,还治痢疾。
还有一种草叫“喜虫蛋”,长一窝窝,很好拽。夏初就结籽,用手挤它的籽,叭叭响很好听。
春风一吹,草儿们都闻风而出。这时麦苗还未起身,不怕踏踩,伙伴们就仨一群俩一伙地到麦田里拽草。等到麦子起身了,“米米蒿”也长高了,夹在麦苗间拼命吸营养。
米米蒿
这时就得专门拔了。脚踩在麦拢间,一根一根地拽。这时没有被锄掉的面条菜、麦秸籽也长高了,结籽了,夹在麦苗间。大人们忙着拔草,我们是一边拽一边还剥开面条菜的籽吃。
“米米蒿”嫩时可以焯焯当菜吃,但后味有些苦,不能多吃。
麦田里还长一种叫“刺芥”的草,学名叫“野蓟”,分大野蓟、小野蓟。田里长的是小野蓟,有凉血止流鼻血之功用。
山坡边、崖头上长的有芦芦葱、叶叶菜,还有一种浆婆婆,汁儿多叶儿旺,兔子很爱吃。叶叶菜一边拽,一边还掐着它的嫩叶吃。
而芦芦葱,好象就是为小孩子长的。叶儿象葱,没几根,主要是吃它的花果。花还是骨朵时最好吃。不知从哪儿传的顺口溜,一边吃还一边念“芦芦葱,上北京,北京城是好收成”。
白蒿
坡上还长一种草,叫掐不齐。我试了很多次,用指甲掐,还真掐不齐。兔子也很爱吃。还有羊奶头,秧蔓长得很长,结的果象羊的奶头,很好吃。
还有白蒿,春天最早露头的草,可以蒸菜吃,药用叫茵陈,治肝炎。我们一边拽,一边念着大人说的“正月茵陈二月蒿,五月割了当柴烧”。还有一种叫“毛狗秧”的草,蒸蒸菜比洋槐花、桐花都好吃。
我家崖上那块地里,长有很多毛狗秧,从春到秋,锄了一茬又一茬,还有很多。我就经常拽了让大人给蒸蒸菜。
春末夏初的田里,多长灰条菜、人仙苗子,这两样都是常吃的野菜。焯焯调凉菜,用蒜汁浇了,非常好吃。现在到饭店里,要一盘灰条菜,最少要你八块呢。
地楞堰边长的最多的是节节草、狗尾巴草,还有一种草我们叫“咕蛹毛子”,长出来的穗子蹭到人脸上痒痒的,可以编小狗、小兔,给小孩子耍。学名叫什么,不知道。这些草嫩时,兔子都吃。
蒲公英
还有一种秃子花,花儿很妖冶,但不知听谁说,秃子花不能拽,拽了会变成秃子。我们见了就远远躲开,从来不碰它。
还有打碗花,说是拽了容易打破碗,兔子也爱吃。但从来没有因拽了打碗花而打破碗的,看来它们没有必然联系。
黄黄苗,就是蒲公英,多长在山坡上、路边,牛踩人踏的,才长得旺盛。蒲公英主要是药用,清热败毒。谁身上长了疖子、痈,或者得了红眼病,拽了熬熬喝,很管用的。还有治妇女奶涨,奶聚住了流不出来憋得生疼时,拽了黄黄苗揉揉敷上,同时喝汁,效果也很好。
那时我们常拽黄黄苗,晒干了卖钱。三毛钱一斤,药材公司收。有一次书店来了一本书,2.85元一本。我想,我要拽多少黄黄苗晒干才能卖两块八毛五啊,想着很绝望。
路边还长枸杞子,枝儿叶儿喂兔子,果儿红时摘下来泡茶喝。路边背荫处、石头下面,还长酸不溜,掐了叶子吃,啊,酸得打牙,越酸越吃。
酸酸草
还有一种草大腿,根长得象鸡的大腿,也不甜也不酸,涩涩的。我们用镰刀剜了吃。还有瓦松,也能吃。
我们整天拽草,也整天吃草,把嘴吃得乌绿。大人见我们这样吃嘴,就骂:“你们是猪?你们是兔子?啥都吃?除了屎不吃!”我们也不恼,我们就是猪,我们就是兔子,它们吃的我们都吃。
房前屋后,多长磨盘盘根,只要有一棵,很快就能引一大片。学名不知叫什么,说是大补。哥哥那时身体弱,夜里盗汗,母亲就用磨盘盘根和公鸡炖了让他吃。
还有岗岗芦,根白生生的,一截一截,也能生吃。还有洋姜。这两样植物现在很少见了。但磨盘盘根还在,夏天回去,看见门前好大一片。小时候感觉稀罕的东西,现在都没用了,一任它疯长,陪伴着荒村老屋。
水芹菜
至于水边的草,那就更丰富了。
猪耳朵叶,肥大肥大的,割一会儿就满筐了。薄荷、水芹菜,兔子是不吃的。但薄荷是药,谁头晕眼花了,揪一片在手心里揉揉,贴在太阳穴或脑门上,立马清醒许多。
水芹菜能吃,投浆水菜最好。有时候拽一大堆拿回家,淘洗后让母亲投到浆水缸里,两天后捞出来,调些盐、小磨香油,就糁子饭,好好吃的。水边还长马莲,折一片马莲叶,编一个草戒指戴上,有时编许多,十个手指都戴。
车前子是少不了的,我们土话叫“车里苗子”,也是一种药,利尿。五月端午采,药性最好。还有一种夏枯草,一到夏天就枯了。
还有一种草,开黄花,夏末秋初,开一河滩,娇艳而伤感。后来我查了下,它叫旋复花。那一年母亲得了肾盂肾炎,医生建议用旋复花煮黑豆吃,效果也不错。
车前草
我们小孩子拽草,有一半时间在玩。提着箩筐,坐在水边河畔或半山坡上,尽情地玩。
眼看太阳快落山了,才慌急失忙去割草,然后虚虚拢拢弄半筐回家了。这时兔子已经饿得在笼子里乱跳,把木头笼子咬得咯吱咯吱。
大人一见就会骂:“死到哪儿去了,看兔子都饿成啥了!”由于整天拽草,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都是绿的,洗不下,就到河边涩巴石头上呲。那时经常想,什么时候不用拽草该多美!
乡野里一年四季都有草。春天春风一吹,小草儿就露头了,我们就拿着镰头开始剜,夏秋季节不用说是草最茂盛的时候,就是冬天,背风向阳的地方,也有草可拽。
除非到了大雪封山,这时就用秋天储存下来的洋槐树叶、大豆杆叶、红薯秧子喂兔子。熬过一个冬天,兔子都瘦得能撂过墙了,只有青草才能让它们吃饱、上膘、增肥。
小蓟
乡村里的草,除了喂兔喂猪外,还有很多用途。一是积肥。
不是有一句歌唱道:“我是公社小社员哪,手拿小镰刀啊身背小竹篮哪,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吗?一到夏天,草长得最旺盛时,我们就割草,交给生产队论斤记工分。那时候很少有化肥,庄稼全靠农家肥,农家肥不够,就人工积肥。
积肥割的草,主要是艾蒿、黄蒿、青蒿这一类杆粗耐实的草。田埂路边半坡上,近处的草都被割光了,得到远处去割。沿着沟渠子割一堆一堆的,到午饭时,往回背。捆一捆子背上,个子小,只见草捆不见人。有的人家用架子车拉,就是最先进的了。
二是当柴烧。那时不但缺吃少穿,还缺柴烧。冬闲时,男人要到二、三十里外去拾柴禾。
拾柴禾也是割些黄麦杠子、白草毛子,还有一种“别别豆”。“别别豆”晒干了,添进灶膛里,会发出“咯咯、叭叭”的响声,很好听,这也是它名字的来历吧。
艾蒿
村里常有女人骂自己男人懒,就说“你不给我拾柴禾,我做饭没啥烧,把你的腿剁剁烧了?”可见柴禾之欠缺。
小孩子除了帮家里拾麦秸、麦茬、玉谷杆、棉花柴、豆杆外,还要割草当柴烧。晴天割些草,晒干了,储备着,等雨天没啥烧了再用。
乡野的草,还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药用。放学后,我们还刨远志、黄芩、柴胡、血参、地丁,还有地骨皮,就是枸杞子的根剥下来的皮,只要土产公司收的,我们都刨了拿去卖。
有一阵子电影上演《春苗》、《红雨》,令我十分羡慕,也幻想当一名赤脚医生,就整天翻开一本《农村医生手册》,看上面的中草药。
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目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它能治什么病。比如门前长的一种开白花的草叫益母草,可以治妇女月经不调,痛经啦,山上长的翻白草,可以治小孩肚子疼啦。
曼陀罗
还有一种草叫洋金花,喜阴,房前屋后都有,叶子乌绿而肥大,开喇叭状白花,结很大的刺疙瘩果。又名“蔓陀罗花”,我是从鲁迅的书里知道这名的。听起来挺浪漫,但气味很难闻,毒性很大。
有一次女伴淑玲说她偏头疼,我就建议她把蔓陀罗叶子焙干揉碎喝。我让她吃一片,谁知她一下子吃了三片。偏头疼倒是治住了,但却中毒了,呕吐、浑身抽搐,把大人吓得不轻。最后送到大队卫生所输液,才好了。
搬着书本,我还采了许多中草药,薄荷、车前子、旋复花、益母草、夏枯草,还有白花舌草等,在门前晒,最后经雨淋发霉都扔了。
现在回到村子,看到满山遍野可爱的青草们,常有一种扑上去拥吻它的冲动。忍不住想去拽,但一想拽那些有什么用?一种失落感袭来,惶惶然。
(图片来源于网络)
推荐阅读
豫记 | 全球河南人的精神食粮
豫记QQ社群:365802781
合作电话:13503998760
投稿邮箱:yujimedia@163.com
豫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