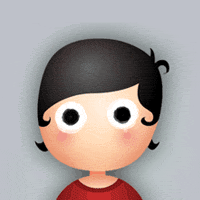武有平:一枚金戒指(小说)
欢迎关注“牛笔文选” 公众号
《一枚金戒指》部分手稿
一
爹早就说,要葬老人呢,不然哪一天我有个一口气上不来,那么多老坟,你们晚辈搞不清楚,没法葬埋,村里人会骂我的。
也是,爹七十六岁的人了,虽说身子骨还硬朗,但人老一盏灯,谁能说清哪一天会灭呢。
按照我们这儿的乡俗,老俩口一方死后先不入祖坟,随便请看阴阳的先生挑一块风水地埋下去,等另一方过世后再刨出先过世一方的尸骨一同往老坟葬。有时因一辈人兄弟多,又想同时葬,里里拉拉的拖来拖去会等到几代人同时葬。我家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我的高祖、曾祖以及祖父辈三代十四座坟都没有往祖坟葬。怪不得父亲这几年几乎把这当成一块心病,常常被折磨得饭吃不下,觉睡不好。
见父亲总是说嘴却没有行动,有时我们兄弟谁遇上就说,要葬就葬吧,有什么难的。在我们眼里葬人无非就是花几个钱而已,现在又不是花不起。
你还年轻,懂得什么。父亲每次说完这句话,就长长叹一口气。
二十多岁上大学时,曾以为自己上懂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世几千年兴衰更替,知识多的了不得,工作十余年,年龄也早过而立了才忽然醒悟自己的知识竟少的那么可怜,早年那种怀才不遇的想法不知不觉逃了个无影无踪。所以父亲说我年轻不懂事我没法辩驳,相反倒是越来越想念父亲的那一大把胡子和苍白而稀疏的头发。但父亲却不肯向我透出一点风声,究竟为什么不早点葬了老人完事。
后来不知哪一天,我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之所以几年来迟迟下不了决心,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我们家正如东方之日,冉冉上升,人丁兴旺不说,继我这个老生子考上大学以后,我的侄子辈中也先后又有几人考上了大中专,爹怕葬人一时不慎坏了风水,于我们子孙不利,所以几年来担着万一葬不了老人挨骂名的风险,不肯轻易下这个决心。
然而这次爹终于下决心了。促成他下决心的原因究竟是自己的身体原因呢,还是看风水的王先生所说的时运好时如何办了如何顺这一理论,抑或二者皆而有之?
深秋的一天有事回家,吃过晚饭,爹说,润保,歇一会和我去你叔家。我问有什么事。嗨,和你叔商量一下葬老人的事。爹说这话时,懒懒地坐在地上的小凳上,背靠着衣柜,眼睛茫然地望着屋顶。爹向来不吸烟,遇上什么需要动脑筋的事时,并不能像书上或影视中那些老人衔个旱烟袋一股劲“吧嗒”,就那么躺在炕上或是靠着个什么物件,眼睛茫然地望着高处,仿佛他所思虑问题的答案就写在屋顶或天空等高处似的。
我也就仿佛刚刚记得自己还有一个亲叔。是啊,爹兄弟两个,且我们这个家庭到他们上一辈时,只传下他们这一枝,葬老人这样的大事,当然应该他们兄弟商量商量。
坐了一会,爹站起用手掸掸身上说,走吧。我就随爹出了门。
爹弓着背走在头里,我轻手轻脚地跟着爹走。七十多岁的爹毕竟年龄大了,精神虽还在,可背是再伸不直了,我这样想着,灵巧地躲闪着才能不踩上爹拖在身后那长长的影子。
说是深秋,一入夜已能闻到冬的气息了。天刚黑,月亮就亮亮地挂在东边,大地泛着一层凄清的白光。风不断从什么地方突然冲出来,在人脸上身上刺几下又躲得无影无踪。路上遇到人都缩着脖子,互相简捷地打个招呼匆匆而过。
润保,爹走着头也不回地说,到你叔家不要多嘴多舌,一切都有我呢。我紧走一步冲爹的后背嗯了一声。
就又走。没有几步,不要多说话,记住没有,爹又说。我说记住了,还想问为什么,但终于没有问。在爹眼里,我这老生子似乎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做什么事都是叮咛嘱咐唯恐我不照办,却很少告我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做,爹带上我这个不准讲话的护卫不是累赘吗?
到叔家大门口了,爹举起手正要拍门,突然把那只枯瘦的手停在半空回头问,润保,记住我的话了。听到我肯定的答复后才拍响了门环。
武有平 摄影(图文无关)
二
叔比爹小两岁,但看上去却像小了七八岁,明显比爹硬朗。叔开门见是爹和我两人,很惊讶很亲热地往家里让。
叔的几个孩子也都已成家,女儿外嫁,两个儿子虽说住在一个院里,但谁都不愿和老人在一个锅里搅稀稠,一大间屋里就叔和婶两人,也没什么家俱,整个屋子有点像刚搬走东西的仓库,大的苍凉。婶一边拿了笤帚扫炕让坐,一边热情地问我几时回的家,能不能多住几天等等。
爹和叔并排坐在炕楞上,我便坐了地上的一只小凳,婶看出我们要谈事,就站在灶火旁,断续地往火里添一把烂柴秸。
哥,有什么事,叔问。爹和叔虽然兄弟只有俩,但因为许多原因,平时基本没来往,没事根本不会互相登门。
我想葬咱的老人,爹说。
今年的山顺吗?叔又问。
我问过阴阳先生了,今年是东西山,我们的坟能葬,爹说。
叔伸伸腰从怀里摸出一颗烟问我吸不吸,我说不吸,叔就放到自己嘴里,又摸出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起来。
半天,谁都没有说一句话。只有一缕缕蓝烟冉冉上升、扩散,变成薄薄的一层罩在我们几个人的头上和昏暗的电灯泡周围。
老二,你说葬还是不葬?还是爹先开口。
你是哥,葬不葬还不是你的一句话。叔漫不经心地吞吐着烟雾。
我们不能让世人骂说高家没有后还是怎么着,怎么连老人都不葬。老二,你也知道,万一咱俩有个长短,将来孩子们根本弄不清那十几座老坟,想葬都没个葬法,你说是不是?
嗯。
哪咱们什么时候去和王先生说一声,让他给看个日子,爹转向叔说。
叔也把快要烫嘴的烟头在脚底一摁,扔到地上,问,是全葬还是怎么个葬法?
全葬,就是指现在已去世而未葬的我们家族所有的先人,而不全葬显然是指我们这一门的老人,因为我的爷爷们兄弟有几个,只不过其他人没有传下后代。这规模不同,开支也自然不同。
这样的话还用问,自然要葬就是全葬了,我正要说话,想起路上爹的嘱咐,就没有吭声。
你说呢,老二,爹竟笑咪咪地反问叔。
我说,是不是先把咱这一门的老人葬了,其他的以后再说。叔说的很不畅快,全不像他平日的灵牙利齿。
全村高家就剩下我们这一门了,那样一做,村里人还不用唾沫淹死咱?往后我们还在村里活不活?爹这一问,叔的脸腾地红了,在昏黄的灯光衬托下,倒颇令对面坐着的我有点害怕。
老大,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一直在灶前站着续柴的婶突然插话说,你不听人说一文钱逼倒英雄汉吗,长才这样说,还不是手里没钱,说话没力,我们家又不比你们家,几个孩子都挣公家的钱,时不时能给家里几个。我们的那两片子儿,没一个成块气的,见天就晓得搜刮我们,长才他说话没根底啊。婶的一张好嘴早听说过,但从小两家来往少,长大后,常年在外,所以我倒还是头一回见识,心中觉得婶这话有软有硬,真有点份量。但我清楚,爹一生除了辛辛苦苦在地里劳作,再没有任何收入,而叔这些年不断做点贩这卖那的小买卖,手头应该比爹活。
老二,到底是葬还是不葬,你干脆说一句话吧。爹依然对着叔说,好象没有听见婶的话。
那一晚谈到很晚,我和爹从叔家里往回走时,月亮开始西斜了,爹一路长叹着,到门口了,终于说,嗨,我知道去不去都是这个结果。
结果是最后婶代表叔表了态,葬人的事是利是害不沾,到时按一般亲戚上礼。
那天晚上好久好久我都睡不着,我想起就在妻怀孕后,一次我们上街去玩,正碰上进城卖杏的叔,好黄好大的杏馋得妻直掉口水,连声巴结说好。可叔却除了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外,连句让吃的假话都不敢说。买又不好意思,气得妻几时提起几时骂我家的亲戚小气,叫我没法还口。现在又……叔,我的亲叔哟!
武有平作品集《倾述》、《真迹》
三
葬人的日子很快就定了,爹捎话让我们弟兄几人先回家刨尸骨。
冬天先我们到了坟地,冷风嗖嗖地往人的肌肤里钻。爹和我们弟兄几人走入坟地不久,我的两位堂弟也到了,只是叔没有到。
爹领着我们烧了纸,点了香,又磕了头,就指挥我们两人一组分头刨。他自己提着大白公鸡,哪一座坟挖开了,就把绑了腿脚的大公鸡扔进去让在里面扑腾,其实是怕里面缺氧,鸡翅膀一扇,空气流通的快一些。照阴阳先生的说法,是驱赶邪气,而且驱过邪气的“扑墓鸡”主家便再不能往回带。
捡尸骨是细心活,粗心人一不注意,丢个手指骨或脚指骨之类的小骨头,岂不等于把先人弄成了残废。所以这件事都由细心的二哥专职负责。
捡曾祖母的尸骨时,二哥忽然对外面的人说,快看,这是什么。递上来的是一个很小的泥环,剔去上面的泥,竟露出一些灿然黄色,是个金戒指,几个人一齐叫道。就有人说,金不锈,银不沤,这上面分明有一些绿锈,怕是铜的吧。爹大概听见了什么或是看见我们聚在一块,也走了过来,接过去说,金子是软的,一试就知道了。说着用力一扳,把个圆圈扳直,再用力又圈圆,说,是金的。说完就装在怀里。
在那一瞬间,我分明看见所有人的目光随着爹的手往怀里一塞时黯了下去。
妻早就要个金戒指,狠了几次心都没舍得买,三百多块呢!但我不会向爹要金戒指的,我们兄弟六人,给了谁能行?再说这一次葬人还不知要花爹的多少积蓄,我不给家里钱已很不体面了,怎么好意思开口向爹要东西呢!
整个下午,我心里反复着这些念头,我自己都不敢保证自己,我是不是对那枚金戒指动心了。
进度明显加快了,大家默默地加劲干,谁都不说什么闲话,也忘了冬的寒冷,只是当二哥捡尸骨开始时,大家的眼就都亮亮的,我不知我的兄弟们想些什么,至少我是希望二哥会从尸骨中再多捡出几个金戒指什么的,那怕有几个银戒指也多好啊。
然而一下午却再没有收获。
武有平 摄影(图文无关)
四
第二天一大早,爹又领着我们出发了。到坟地时,叔和两位堂弟已等在那里。叔迎上来问,哥,来了。嗯,你今天不忙了。爹说。家里有些事,好不容易才脱开身,叔讪讪地说。接着又分头行动。叔和爹是长辈,所以也不动手挖,只是哪一座坟挖开要捡尸骨了,他便急急的踱到跟前,眼光刺刺的盯着二哥的手,直到捡完最后一根尸骨。但这一天再没有挖出一件值钱的东西,有那么几件粗糙且平凡的酒盅酒壶也不是被不小心碰掉了嘴就是裂了缝。
第三天,请了人去祖坟地挖葬墓。请的响器班也来了,院里用大树根生了火,唢呐就吱吱哇哇地吹了开来,里面还夹杂着二胡和芦笙,来一拨客人就吹一番。调子是没有固定的,竟全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十五的月亮》、《望星空》等等,唢呐一抖,二胡一揉,现代派歌手们歇斯底里的歌竟变成悲悲戚戚的哀歌,真令人不可思议。记得从前的响器班并不用二胡和芦笙,可能也是在引进在改革吧。
爹不愿大张罗,就没有请总管,谁知里里外外竟忙得不可开交。我在家里是老生子,大家都认为我办不了大事,就分配在院里照应响器班和要饭的。快中午时,叔来了,问我爹在哪里,他有句话要问。我告了他,一会就见爹和叔相跟着走进一间空屋。
不一会,忽然听见爹嚷了声“哪里来的这理”。这句话嚷得很响,那呜呜哇哇吹打的曲子竟没有盖住它,使得它如同突然冲刺的北风一样迅捷地走遍院内的角角落落,传到院内的每一个人耳中。接着,就见爹愤愤地从空屋里出来,叔在爹后面跟着,脸上不尴不尬,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爹一边走,一边头也不回地说,你拿去吧,你是老生子你牺惶你可怜,这老人你也都拿去吧,我不管了。叔还是跟在爹后面走,一只手紧紧攥着。我急忙跟在后面走进家里。
阴阳王先生正在炕桌上戴副老花镜往砖瓦上画符。爹一进门,气汹汹地说,王先生,这两天白麻烦你了,回头再补报你,这人我不葬了,谁愿葬谁就去葬吧!我一看势头不对,忙走过去,爹,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不用你管,你懂个甚,爹没好气地就是两句。这时王先生也反应过来了,搁了笔说,长生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行吗,,火气这么大。王先生毕竟是先生,在这一方土地叫得很响,年龄大,资历老,说话锋芒毕露,凡人谁不让他三分。爹指着叔说,你让他说,开始要葬人,他怕花钱不同意,推三阻四的,最后说了是利是害不沾手的话。现在听说刨出个金戒指,眼红了,说甚我是长子,享受的家产多,他牺惶他可怜,想要金戒指,那就让他拿上金戒指去葬人吧,反正我是不管了。
正在不可开交,婶忽然闯了进来,指着叔就骂,你这老不死的,穷得你剥皮啦还是抽筋啦,一个金戒指就能救了你的命,怎么跑到这里来丢人现眼!骂着,就伸出手掌问,你把金戒指拿去了。叔那只紧攥的手在婶手掌上空一松,黄灿灿的金戒指就掉到了婶手里。这时,家里又是自家人又是亲戚还有一些挤进来看热闹的人,挤得成了一锅粥。作为乡下出生的人,我没理由讨厌乡亲们的贫穷落后和愚昧,因为我曾是或者说现在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我实在讨厌乡邻们那种唯恐别人家里不出事的劲头,谁家嫁娶要去看,丧葬要去看,吵架了要去看,甚至谁家来了个生人也要去看,即使在经济信息方面再愚钝的人也会在这一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听觉、视觉和嗅觉,任何一点红火都不会放过。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我感到脸上臊得很,心跳也似乎加快了一些速度。但婶不顾这些,走到爹跟前说,哥,你也不是不了解长才,他这人就是不会办事,说出的话,泼出的水,男子汉说话如同写下,怎么能说好是利是害不沾手却跑来要金戒指呢,哥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全当他是放了个屁,还是妥妥贴贴把咱的老人安顿了吧。说时就把那个金戒指伸到爹面前。但爹好象没听见,也没看见,竟丝毫都没有理。
这时王先生就走过去说,长才家的,把戒指给我,你和长才先出去一下。就接过戒指劝爹不要耍脾气。后来母亲也过来劝,但爹就是不改口,半点都不让步。
按说遇上这种情况,阴阳先生丝毫没有责任,完全可以大大咧咧走掉,最后还需主家重新请。但王先生却不,他先出去把闲人都赶出院关了大门,又把我们堂兄弟姐妹一大帮以及其他内亲连同带来的孩子叫到一起训了一番话,便带着我们进了屋。一进门,大家都依照王先生的指示,卜咚卜咚跪了满满一地,在大哥的带领下,爹、伯、舅、爷爷老爷的叫成一片,都说您消消气吧。但爹纹息不动地站在那里。王先生就命令我们先出去。接着是叔和婶被王先生领着进去又领出来。最后王先生领着爹的娘家舅家一干人和母亲走了进去,爹见娘家舅家的人跪了一地,再不敢无动于衷了,终于长叹了一口气,卜咚一声跪在对面说,我长生连累你们了,说时老泪扑簌簌掉了一大滩。
就在这时,不知是王先生还是谁的安排,唢呐一声激越的调子飞出,接着锣鼓铙笙齐奏,人们心头的最后一点阴影就随着这激越的乐声跑得无影无踪了。
武有平 摄影(图文无关)
五
第二日天还不亮,人们就簇拥着随着响器班出发了。天阴得黑沉沉的,没有风,并不冷,偶尔飘飘扬扬地飞着几朵雪花,也一落到人身上就化了。我走在爹的身后,仔细看爹走路,我忽然意识到,爹怎么几时就老成这样子呢,那宽宽的背几时竟驼成这样子呢,那不是我儿时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吗……唢呐声声,我的思绪却很难集中到眼前进行的事上。
到了坟地,便是往葬墓中安放尸骨。王先生指挥着安放什么五色石、牛皮以及画了符的砖瓦之类的镇物,接着是点灯,插香,要封土了,便让所有孝子人等都站过一旁,王先生拿了引魂幡站在墓穴前,口中念念有词,请接引佛前来接引死者亡魂,然后引魂幡一甩,一招,用手从幡杆上把写有死者姓名的幡儿一把撕下扔进墓穴,请来打墓的人便一齐往穴中填土。
最后只剩爷和奶的葬墓了,王先生撕下幡儿扔进墓穴,正要喊封土,爹突然上前,伸开手掌说,爹,娘,这只金戒指几乎闹得我们兄弟不和,留着它,子孙们还会出事,现在就交给你们吧。说着,顺手一抖,就在众人眼前把一枚黄灿灿的金戒指扔进墓穴。又说,封土吧!很快,祖坟里又多了一座新坟。
不遇特殊情况迁祖坟,葬墓就永远再不往开打,爹的这一手谁也没有料到,一枚金戒指就这样永远和我们告别了。
同时埋下的七座新坟,一般高,一样圆,除了知情的人,谁会想到其中一座坟里面有枚金戒指呢!
起风了,雪纷纷扬扬地挥洒起来,很快便铺满了整个世界。
(注:本文原载《吕梁文学》1993年第四期,1994年第八期《山西文学》发表时编者更名为《全葬》,后收入作者小说集《真迹》时恢复原名)
武有平(2009年摄)
作者简介:武有平,山西方山人。1965年生,作家、书法家。
一、《牛笔文选》欢迎赐稿。
二、在其他平台发过的作品,请勿再投。
三、投稿邮箱:360867029@qq.com
四、《牛笔文选》平台赞赏: 赞赏累计不足10元的,不予发放。60%为作者稿酬;40%留作平台费用;
欢迎关注,欢迎赐稿。
投稿邮箱:360867029@qq.com
本文系作者授权“牛笔文选”微信平台发布,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