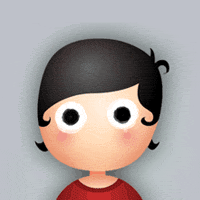你与好故事,只差一个关注的距离
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签约作者:苏汴州
禁止转载
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朱红的戏楼里妆面秾丽的戏子所唱端的是一曲家喻户晓的《牡丹亭》,搭袖、拧身、碎步……身段姣好的戏子明眸皓齿,顾盼生辉,一举一动彷如杨柳曳月,两丸乌沉沉的眼珠子只消一睇,就自有勾魂摄魄的魔力。
触目可及尽是红彤彤的灯笼,照得空气似溶溶流动,台下票友满座,叫好声此起彼伏。时局正乱,人却最是擅长于其中讨些乐趣,正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
二楼包厢显是来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那轻飘飘的紫纱帘子已经进进出出好几个捧着瓜果茶点的丫头,人人表情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恐有一丝疏漏,包间门口还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魁梧挺拔,一丝不苟。
这年头,打仗的比打粮的多。
一曲唱罢,台下掌声雷动。戏子盈盈谢了幕,往后台去。
郁秋摘了一头珠钗,褪下戏袍换了件白绣牡丹的旗袍,正要离开,不料迎面撞上唐肃轩。她不动声色退了两步,手心却已经发了汗,手袋似是千钧的重物,令她不安。
得罪不起,只好笑脸相迎,“唐公子。”
唐肃轩狭长的眸子里是寒意森森的笑,“邱小姐好本事,居然躲我这许久。”
郁秋的惧意越发深了,又轻轻退了一步,强挤出一抹笑,“唐公子哪里话,多得是想黏紧您的人,我又何至于如此不识抬举?”
唐肃轩轻笑一声,“既然你情我愿,随我走!”说着一把箍住她手腕就往外拖,她挣扎起来,奈何根本挣脱不了。唐肃轩用了极大的力气,恨不得捏断她的腕子。
绝望中看到梳妆台上的茶具,她奋力挣开一只手,抓起一只杯子就往他头上砸。他却是早有防备,头只略略一偏就避了开,杯子“咣”一声碎在地上。
戏局已散,厅里早没什么客人,唐肃轩一路拉着她就往前门走,郁秋不管不顾地大喊。台上倒还有几个戏楼的工作人员,班主甚至就在其列,郁秋恐惧地呼救,所有人却聪明地别开头去,没有人敢惹这位唐家的二世祖。
恐惧和绝望笼罩下来,郁秋泪眼朦胧却只能眼睁睁被唐肃轩拖到车前。
“唐公子。”
暗夜里一双深邃幽暗的眼睛静静凝着唐肃轩,来人一身戎装,身形颀长,军装极为挺括,帽徽在黑暗里隐约有粲然寒光。
郁秋怔在原地,如五雷轰顶。
唐肃轩脸色微变,“原来是林司令,适才我还在想那二楼包间究竟是哪路神仙,竟然用了那样大的场面。”
林鹤唳趋近两步,走出了暗处,长相分明是芝兰玉树的公子,却无端端令人生出惧意和瑟缩,“这是要去哪里?”淡然清浅的眸子往唐肃轩抓紧郁秋的手上一划。
时局虽乱,堰城却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地方,因那帅府屹立不倒的从来是林鹤唳响当当的名幡。虽有八方势力云集于此,,若说跺跺脚就能影响全省气候的,掰着指头便数得过来,这位靖国军司令部林司令更是一顶一的一位。
唐肃轩不能不答,口气却是不荤不素,“回家。”
林鹤唳眼里却忽然有了一丝玩味,“鄙人扰了唐公子的好事?”
唐肃轩回头看了一眼郁秋,说得很是直白,“现在还不算,但您若再拦着,那就是了。”
林鹤唳恍然大悟般“唔”了一声,旋即唇角一勾,声音极沉,“这位会是您的几姨太?”
政府职员是禁止纳妾的,林鹤唳此话分明戳到了痛处,唐肃轩明显恼了,眉心攒得紧紧。他的父亲也是得意非凡、钟鸣鼎食的显贵人物,平日却不得不仰这位年轻将军的鼻息,今日他又在他这儿横插一杠,这种窝囊气他唐大公子何时受过,一句冲动话脱口而出,“林司令怕是管得宽了些!”
唐肃轩的侍从官却是极乖觉的人物,几乎是以下犯上的口气,“少爷!”此时孰重孰轻,他还掂得清。
郁秋微微蹙眉,明显感觉手腕被盛怒的唐肃轩掐得血液几乎要不流通了。
林鹤唳噙着笑,神情却生出几分凛冽来,“若我说我也中意这位小姐,不知还算不算管得宽?”林鹤唳淡然开口,语气飘忽不定,难辨真假。
郁秋蓦地抬头,正对上林鹤唳情绪莫辨的眸光。
唐肃轩发了狠,咬牙切齿,眼睛死死锁定林鹤唳,当中分明是夺妻之恨。
半晌,他泠然松开手,大力把郁秋往前一提,她站不住脚,被搡得失了重心,直扑到林鹤唳怀里。他身上有淡淡的烟草气味,熟悉到她几欲落下泪来。
他也沉下眸子看她。天地恍惚间,她怔怔凝望着他眼里坠落的星河,如同星光璀璨的海面,跳跃着浮金一样的光斑。但旋即,他眼中那皎皎辉色却迅速黯淡下去,如同匆促划过的流星。
夜风一吹,她骤然惊醒,他却早不着痕迹侧开一步。正红的灯笼在檐下晃动,在她看来却如同一张张血盆大口,恨不能在她千疮百孔的心上啮噬几口。
唐肃轩阴瘆地说:“若林司令有这癖好,不过女人,我让给你又有何妨?”
说着大力拉开车门,扭头上车,脸上犹结着寒冰,吩咐道:“开车!”
轿车绝尘而去。
他回过头来,薄冷的黑瞳如同深水漩涡,吸住她的眼睛,令她避无可避。
“郁小姐,好久不见。”公式化的问好,不夹杂丝毫情绪。
心中似有小小的希冀化为泡沫,郁秋无限悲凉地一笑,“这三年,你过得好么?”
他冷笑,眼神似讥似讽,“你当知我过得好不好。”
她突然心灰意冷地垂下头去,无论故事的发端是谁的错误,但故事的结局却是她对不起他。那四年,他爱她如命,用尽了心思和手腕,她却以死相胁,逼他寒透了心,斩断了情。
原来今夜之事,并不是什么余情未了,只不过是一阵恻隐,于她如此,想必他于一只猫一只狗,亦是如此。
她的声音如蚊蚋低微,“谢谢您。”
事已至此,多说何益?
她这个样子却不期激怒了他,一只力道十足的手夺过她的手腕攥住,逼得准备离开的她正视着他。他的目光像利剑一般,戳得她满身俱是鲜血淋漓的窟窿;他脸色铁青,咄咄逼人地盯死她,连额头的青筋都暴了出来,凌厉的怒气喷涌而出,眼底却是血红的一片。
他的嘴角抽搐,终究未说一语。
良久,他忽而笑开,笑中尽是悲怆和凄然。
他蓦然掉头而去。
她哽咽着蹲下,凝望着他径直离去的背影,西北的朔风穿堂而过,她把脸埋进双膝之间,紧紧抱起,只剩肩胛在风中抖得那样厉害。
2
梦魇。
她苍白的脸泪意莹莹,眼中却是决然,“放我走。”
他的眼神可怕极了,往前拾了一步。
“咔嗒”一声,那是他最熟悉的枪开了保险的声音,他苍凉又不可置信地蹙眉看着她。
她的眼睛像沉潭里的水,没有一丝波纹,一把小巧的勃朗宁正正顶在她自己心窝的位置。
难道和他在一起,竟比死还令她苦楚?
彻骨的寒意涌上心头,他平生花费最大心智做的一件事,到底是没能如愿。他曾以为努力终会改变她的态度,让她爱上他,可他却是错了,她不爱他,一点都不,她甚至厌恶他。
他一生称意,翻手为云覆手雨,可他用尽了所有力气,掉光了所有身价,这一切在她的眼里,居然一文都不值。因为他爱她,他已在她面前一败涂地,今日,她却还要再判他死刑。
他忽感无力,民国九年他战场败走,现今想来,人生的唯一败绩竟还不如此时痛不欲生。
他猝然退了几步,脚底却是虚浮踉跄,他的眼里一片枯败,那样绝望的神色让她心生了惊悸。
一道惊雷撕碎夜空,雨声汹涌,疯一样砸在窗上。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颓垣。
如同几将溺死的人放弃了最后的挣扎,他用尽垂死的力气从齿缝里一字字用力挤出,“我,给你自由。”
突然就醒了。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一支凝神香烧了一半,暗沉沉的夜色里融进了苍白的雪色,依稀看见烟气袅袅,婆娑洇开。
他定定地躺在床上,神情萧索。
3
初见她时,她唱的还是那支《牡丹亭》,那时他已是有名的第三混成团的团长,在军中威风凛凛,声名赫赫,在外亦欠下不少风流债,名媛淑女趋之如过江之鲫。
那时他作风另类,全不似城中其他青年权贵,因为受了严苛的家教,处处拘着手脚,生怕玷污了祖宗门楣。他不同,农村出身,父亲是个木匠,替他做出第一把木刀时,他伙同几个小伙伴在关老爷像前咚咚磕了几个头,拜了把子,扬言要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当时母亲拎着他的衣领子把他捉回家时绝不会想到,多年后温良的儿子会变成“关西刀客林一刀”,后来参了军,又是战场杀伐如阎罗的铁面司令林鹤唳。
他在战场负了伤,回坤县是为休养,他却并不安生,好容易消闲便每日纠集一帮公子哥打牌宴饮,骑马郊游。
听闻梨园上了新戏,一帮人呼啦啦全涌到戏园子,戏子出来时他却怔了一怔。露天的戏台开满繁盛的海棠,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地拢在一起,那香气罩着他恍恍惚惚,昏昏沉沉,如同飘在云巅一般,目眩,并且神迷。
他只觉得耽在那戏子莹莹一双眼波里,逃不脱,也不想逃脱,戏子口中的空谷之音全成了那如花眼眸的背景和烘托。那女子一拢眉,一颔首,一颦,一笑,无不使他心旌摇动,即便战场杀伐早使他情绪内敛,滴水不漏,同行的宋家公子却还是瞧出了端倪。
那宋遥是何等警敏慧黠的人物,闪电速度就将郁秋送到了帅府。那时他大概知道宋遥是使了些手段的,但内中详情他并不想关心,人生头回他对一个女子产生魔障般的兴趣,只要结果达成,过程怎样又有什么关系。
现今想来,也许那正是错误的开始。
英武将军与美貌戏子的璀璨婚礼曾占据许久的报纸头条,多少豪门名姝伤透了心,咬碎一口银牙。她们自诩比那风尘戏子矜贵太多,但临风而立的林帅中意的,却偏偏是那下贱蹄子,这叫她们不屑中更多是羡慕,鄙夷中更多是惊恸。
他曾在婚后他度过了人生最幸福的几年,尽管那期间郁秋不笑不闹,眉间也总是疏离,如同笼着淡淡的轻烟。但只要郁秋眼中稍有涟漪他就兴奋不已,只要同他多说几乎话他也几乎彻夜难眠,他像个毛头小伙子一样一腔孤勇、不计回报地投入爱和耐性,飞蛾扑火般不回头地撞向自己以为的幸福。
那段时间,林鹤唳周身素来的寒气像是春雪见了太阳,不仅荡然无存,整个人还如同浸着温颐之气。甚至碧县遭劫,他也只是饬令全力驰援,并没有如往常一般暴怒,殃及众多池鱼。
4
他清晨才带着一身露水回家,黑色的轿车箭一样划进镂花门,车子还横在庭前他就飞掠上了二楼。
郁秋浅眠,立时坐了起来。
“别怕,是我。”他轻笑,一张脸衬着青白的天色,越发明朗濯濯。
“这么早?”她目光温和,神情却是一贯的淡然。
林鹤唳不以为意,从背后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小小的锦盒,笑着示意她打开。里面却卧着翠绿莹莹的一只手镯,玉色通透,没有半分匠气,那抹碧绿似乎隐隐挥发开来,浸润在空气里。
“生日快乐,”笑一笑,“能拔得祝贺的头筹,也不枉我这一晚上驱车的辛苦。”
郁秋看他眉毛睫毛上都凝着霜,于是含了笑,一双梨涡浅浅而现。
林鹤唳几乎看痴,他心下一喜,不等她开口立即说,“我知道你不爱西餐,就差人定了苏菜,‘春风渡’的平桥豆腐你一定喜欢。”
不等回话,他又惶急地说:“我竟忘了,现在时间太早,早餐一定要吃的,不如让下人做?”
郁秋心酸,林鹤唳天潢贵胄般的人物,半生顺遂,何曾谨小慎微至此,勉力又一笑,“好。”
那时春刚至,空气里混着诸多花香,餐桌上偶听得银匙一响,林鹤唳只觉得声音清脆,妙不可言。
然他不知,从来都是彩云易碎琉璃脆。
那只春水般的碧玉镯到底被砸碎在地上,粉身碎骨。
他站在那里,石像一样纹丝不动,眼睛如同要滴出血来,五脏六腑似被一把钝刀一刀刀锯开,再一刀刀绞碎。
她浑身发抖,面如死灰,撕扯着他,紧接着便是狠狠一掌掴过来,耳中嗡嗡作响。他却下意识出手托住她,免得她情急下踩上刚才砸破的花瓶碎片。
她泪如雨下,细瘦的腕子扯住他的领口,却双唇颤抖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尸体呢?”
他痛苦地闭眼,“路途太远,葬在了关山。”
郁秋嚎啕大哭,灯下瘦削的肩膀簌簌发抖,令他心里泛起疾痛。
他伸手触摸她的头发,她却猛地一缩,眼中是露骨的憎恶,他的眼里立刻就浮现伤痛之色。但郁秋只是哭,他曾命园丁为她悉心培育的名种百合沿廊台蔓延出去,素白的花瓣却被一场秋雨浇成了颓败的浅褐,绒绒的花蕊被骤雨打落在地上,混着雨水汩汩流远。
他神色沉痛,声如呓语,“原来宋遥一直以你弟弟做要挟……”他精疲力竭地垂下手去,“我的错,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他几乎逃一样回到了军营。
他强迫自己不看不听不想,日日没命地溺在公务里,练兵,开会,酒局……他甚至约电影明星裴慈慧一起游了一趟湖,裴慈慧盛装出席,艳丽的脸上妆容精致,谈笑得宜,他却只觉得兴味索然。有些事、有些物,你越想忽略就越会清晰浮现在眼前,剔骨剜心一样地疼。
又是一场宿醉,他酒量再好也受不住这样玩命的喝法,他踉踉跄跄地拾阶而上,侍从扶他,他的力气那样大,直搡得侍从背撞在窗台上,惨叫了一声。
廊子里亮着昏黄的壁灯,一盏盏似孤独的花,孤单单开在黑夜里。他扶着墙壁,一路走一路皱眉,为何会这样长——长到根本走不到头,长到他力竭也无法到达,长到他费尽心神、机关算尽,却只能是自欺欺人。
电话急促地响起,他的额角突突直跳,喝道:“给我掐掉!”
他的发际汗意涔涔,风卷着窗纱灌了进来,他愈发恶心难受,一手无力地扯着领带,一边却喃喃,“秋儿,秋儿……”
门“砰”一声被大力推开,侍从贺少康红着一双眼,“司令,夫人出事了!”
5
他回来时已经晚了,陈医生的那通电话是他自己摁掉的。
她面色惨白,满室都是血腥之气。
他鹰隼一样的目光将她钉在原地,呼吸声急促如抽泣,暴怒的他攥住她的领口,医生大骇,七手八脚地去掰他的手。
“司令,夫人小产后身子正虚。”
这一句提醒却如同开水溅入滚油一般,摧枯拉朽一样一刀豁开他骇人的恨意。
他猝然将她拖到眼前,眼里的怨忿和痛苦展露无遗。
郁秋只觉得四肢百骸都在痛,肚子更像被一把铁锤一锤锤地砸,她的眼神却是最容易激怒他的疏离与凄清。
良久,一滴泪划过他深刻的五官,惊得郁秋内心一悸,“为什么?!为什么?!你就这么恨我?!”为什么她这么恨他,恨到能亲手杀了一个尚未成形的孩子,一个她和他的孩子——一个他的孩子。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灼得她面部生疼,心中似乎有什么崩然断开,“是。”却又是一波汹涌的泪水。
蚀骨的绝望终于将他淹没,他突然发笑,如同受伤的孤魂野鬼,笑得惨不忍闻。
她就这样践踏了他所有的心意,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而他竟然如此卑微,如此自贱,如此被她玩弄于鼓掌,却之如饴。
他活该。
他的手指颤抖地指了指碎在地上的那支镯,眼神里已是一片寂灭,“这是我母亲的遗物。”
她的心狠狠一颤,却像孤注一掷一般,咬牙说:“我知道。”
他蓦地扬起手,她本能地捂住脸,以为他要打她,他冷声一笑,眼眸里是再溅不出一丝火星的冰冷死灰。
他伸手,“你将那装镯的锦盒还给我,那是我父亲为我母亲亲手做的。”
他垂下眼去,用尽毕生力气,“我们离婚吧。”
6
花圃里的桃花开成了百合,百合变成了菊花,菊花谢了又是一树落落的荆叶梅。时间如水,划过了人的手掌,凝成了冗长岁月里微乎其微的叹息。
郁秋在堰城已经三年。
当时她孑然来到堰城,只能重操旧业,期间唱过杜丽娘、祝英台,扮过蝴蝶梦,窦娥冤。她在一方戏台上碾过了三年的光景,百里外林鹤唳的名头却是更加显赫,姑娘们红着脸碎碎念完他的英明神武,总会提到他“不知好歹”的前妻,也总会捂着嘴娇俏地惊呼,“邱姐姐跟她好像!”
当年的报纸一版再版,哪个小姑娘手上没有一张旧报纸供闲时瞻仰那冷峻将军一番,但她们绝不相信那般人物的娇妻会是与她们一起挤在阴冷鸽子笼里清瘦的邱姐姐。更何况,那林太太有极其凄婉的名字——郁秋,姐姐的“邱秋”与之相比,到底寡淡了些。
堰城邵家长孙的满月酒,阵仗极大。
郁秋在后台穿戴,绍芝蹿进来,收势不及撞在桌上疼得龇牙咧嘴,顾不得揉一下气喘吁吁道:“姐姐!邵家居然请了唐次长和唐公子!”
她却并不慌,只是苦涩一笑,林鹤唳什么做派众人皆知,既然他已经插手,就算再借百个胆子,那唐肃轩也不敢逆他的鳞。
笙箫起,郁秋提袖盈盈上前,琵琶声声入耳,台下言笑晏晏,宾主尽欢,孩子在席间笑闹,声音又糯又甜……然这于她,又有何干?
忽见首席几个人噌地站起来,邵老爷更是笑容可掬地往照壁走,鼓乐声戛然停了,郁秋也敛了袖子,循着望去。只见回廊上众人拥着一个人徐徐而来,来人笑意盈盈,簇在人群中越发显得长身玉立,不是林鹤唳又能是谁。
郁秋心下一惊,背心已渗出虚汗,她知邵老爷也在政府中任职,因此一早就打听过,不过是边缘职位,触不到核心要务,也断然不会惊动林鹤唳,然而她千算万算,没料到林鹤唳会不循常理,不请自来。
因着林鹤唳来,邵老爷得了天大的面子,笑得合不拢嘴,场面越发鼓乐欢天,其乐融融。
热闹一直延续到月上柳梢。
郁秋身体不好,折腾这一天精神极差,再加之林鹤唳在台下,那戏台便像脆薄的冰面,她只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他的眼睛又如兽金的炭火,似乎要在她身上烧出个窟窿来。冰火两重天,她经不起这样的消耗,只觉得头晕目眩,像踩在云上一样轻飘飘出了邵家。
却不小心踢到了门槛,几乎要绊倒的瞬间,迷糊中一双有力的手大力拽住她,她晕沉沉地抬头看,林鹤唳一双眸子在黢黑的夜色里愈发幽远疏阔。
“你弃我而去,就是为了今天在这里倚门卖笑?”林鹤唳一身酒气,一张口就是极伤人的话。
她被他羞辱般的用词一鞭打在脸上,脸色苍白如雪,忽地抬头逼视着他,眼里却如同浸透了血。
她死死盯着他半醉半醒的眼睛,心中似被一双巨手攫住无法呼吸,只留铺天盖地的痛楚。原来她在他的心里竟如此不堪,与那人尽可夫的娼妓并无太大区别……
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弟弟还在宋遥手中,她为何要爱上这个恶魔,那时貌似是她残忍斩断了他的情愫,但痛不欲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
孩子胎死腹中,她听见他在书房隐忍压抑地恸哭,心中如被尖刀一刀刀扎成筛子,她从不会谋杀亲子,孩子不过是她心绪不稳所丧。她知道这是报复他最好的机会,当时她却生了迟疑,她不想他那么伤心,那样悲绝的声音像重拳一样拳拳击在她心上。
姹紫嫣红都开遍,她不过是他一时兴起随意摘下,她理当像个宠物般摇尾乞怜,可她却不知好歹,失了圣宠。三年后,一朵野花再入不了他的青眼,在他眼里,她只配以色侍人,倚门卖笑……
她笑得泪花溢出,疼得肝肠寸断,那邵府朱红的大门似要绞出血来,滴破这漫天大雪,痛和冷齐齐袭来,只余一片枯槁的麻木……他的脸终于渐渐消失在深沉的黑暗中。
7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春梅小。
暮春时节,花园里色彩斑斓,合该是姹紫嫣红皆开遍。绒绒的棣棠,雪青的杜鹃,鸟喙般的连翘,最繁茂的是一簇簇的仙客来,远远望去竟像跳跃的小小篝火,又像怯怯伸出的圆润兔耳。心形的花瓣吸透了露水,羞涩垂下头来,郁秋清浅一笑,原来连花都有羡煞旁人的幸福。
可她,却什么都没有了。
她被关在这豫园里已经三月有余。
她犹记得大醉酩酊的林鹤唳死死抓着她的手,将她狠狠拖进豫园,面孔几近扭曲,眼神里痛意骇然,低咆道:“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我不会再放手!你休想再离开我!孩子我不要了!镯子我也不要了!”
他的声音忽然低下去,像是被谁掐紧脖子,只从胸腔最深处发出嘶吼,“我一直在找你,整整三年,好容易知道了你的下落,你却在百里之外,为了升职,为了能来堰城,战场上我豁出命去,每每与死亡擦肩而过时,我总在想,我离你又近了些。”
醉酒让他错乱,他突地欺身上来,一把钳住她的脖子,如一头复仇的野兽,杀红了眼,只剩怵目惊心的恨意和杀意,“可你还是不要我……”他像受了重伤一样,面色如雪,瞳孔缩紧,手也越收越紧,她被生生夺尽空气,只觉得天旋地转,头昏目眩,意识开始游离神智之外……
突然,他像被烫到一样缩回了手,怒瞪的双眼里满是匪夷所思,他看着剧烈咳嗽的她,像是不认识一般,喃喃道:“他们说得对,说得对……我自甘堕落,我失心疯……”
世家公子那么多,关系一般的尚且劝他一句,经常腻在一起的更是痛心疾首地骂他“中了邪,着了魔”。在他们眼里,这样一时无双的人物难道会缺一个女人?
姹紫嫣红皆开遍,可独独春草般孱弱的她长进了他心里,这春草在他心中燎原,在他的心里攻城略地,不留一丝空隙。他曾试着薅锄,可到底春风吹又生,他只得缴械投降,放下原本就残存无几的自尊和傲慢。
心晦涩至极,几乎已经丧尽呼吸的力气,他的眼里闪烁着暴戾和冷绝,“休想再跑!如今你既不让我活,那你就是我的陪葬!”
摔门而去。
三个月来,再无半点音讯。
她每日睇着日光从窗棂上轻轻跳起,又从阳台上沉沉坠下,鹅黄,赤红,蟹青,黧黑……千般色彩在天空变幻,在她眼里却不过瞬间。日子就这样絮絮过着,她如同一缕轻烟,丧失了对四季和时令的感观。
佣人却是多嘴的,岭南的橘子,和福居的点心,锦绣庄的旗袍,东家的翡翠西家的玉,都是司令“特意”差人送回来的。话里自然真假参半,但衣服的尺码,食物的口味正适合她却是无疑。
8
晚餐照例是一个人的席面。天上凝着黑压压的云,墨色浓烈欲坠,许是要下雨,空气沉闷异常。
勉强生吞下几口饭,胃里依然一阵难受。索性不吃了,刚走到楼梯处,佣人忙唤,“夫人,信。”
看到封蜡她脸色就变了,抖着手几乎撕不开封口,一道惊雷轰一声照亮她惨白的面孔,她魇住了一样死死盯着信纸,佣人见她神色不对,急忙上前,“夫人!”
她恍惚地抬起头——下一瞬忽然泪如雨下,嘴唇哆嗦着,“怀书,还活着。”
她抓紧栏杆,似乎撑不住自己一般,声音飘渺空洞,“备车……快去……”
指挥部本极其简易,但因为主人挑剔,林鹤唳的卧室安了厚重的胡桃木门,此时那木门泛着莹莹黑褐,抛线花纹如同一个个浅薄的漩涡。
她到底没有勇气敲门,那么近,又那么远,这一道门于她而言,是四年的心不在焉和三年的抵死痴缠;于他而言,却是四年的精疲力竭和三年的无法释怀;于他们而言,已是万难逾越的天堑。
宋遥看出林鹤唳对郁秋的不同,威逼利诱郁秋的胞弟郁怀书暗中策应他,郁怀书亦是男儿铁骨,自不愿同流合污,便诈死脱身。宋遥虽没找到郁怀书尸体,却不敢得罪林鹤唳,只得谎称郁怀书已死。郁家姐弟失散,郁怀书又颠沛流离,不敢太露行迹,延宕这多年才找到郁秋。
郁秋苦涩一笑,一滴泪无声落了下来。
“叮——”一声电话铃响,军靴在地面上敲出笃笃的声响,郁秋一颗心几乎提到嗓子眼,她凝神屏气,生怕室内人察觉出来异样。
却是侍从贺少康的声音,“裴小姐?”
“是的,司令不在。”
“真的不在。”
“您知道他的脾气,您这样做可知道后果?”
“这话不是我说的,司令让我转告您,不要纠缠。”
“您不要哭,您并不是第一个被拒的小姐。”
“裴小姐,您不要为难我。”
“司令从来只有一位夫人,他从坤县杀到堰城就只是为了她。”
“您若不信我没有办法。”
“他有多宝贝那锦盒您不是不知道!”
“恕我无能无力,裴小姐,若我帮您必定会受军法!”
“装的是——夫人的一绺头发。”
断断续续的通话郁秋却瞬间听明白了大概,周围的一切忽然开始飘渺不真切起来,所有的脉络终于连成了完整的一片,支离破碎的片段交织成故事完整的梗概,她的脑子嗡一声,只觉得孤身行于海上,天昏地暗。
“砰”一声巨响,贺少康惶然回头,看见郁秋立在门口,泪光泫然。
“他呢?!”
9
静。
静得能听见输液器液体一滴滴垂落的声音,那样轻微的声音却像一把锤子一样一下下砸在人心上。
除非天塌下来,否则林鹤唳怎么会擅离职守,留贺少康在指挥部应急。
的确,防御工事塌了。
一场暴雨,他带工兵修筑工事,大雨中墙体狠狠砸下来,亏得他身手矫健,但还是受了重伤。
郁秋凝眸看他,他沉沉睡着,眉头却紧紧蹙着,医生说他刚服了药,需要休息。
他穿着病号服,周身再没有平常的戾气,那摄人心魄的眼睛阖上后便只是俊逸非凡的普通男子。垃圾桶里是带血的纱布,他的左手无力地垂着,右手却紧紧护着那只眼熟的锦盒,拢在胸口。
她冲动地伸出手去,到底是重伤,她并没有费太大力气就拿到了盒子,她想起那时他哄她打开盒子时眼里眉梢朗润的笑,心里一拧,竟像含了黄连在嘴里,苦涩难捺。
果然是一绺头发!色泽质地证实了主人无疑是她。
她掩住哭声,生怕惊醒他,贺少康说,“那三年,司令手中最常抚着的不是配枪,而是那只盒子,旁人只以为他纯孝,感念父恩,只有我知,他会拥着盒子失眠,醉了会把那物件狠狠掼在地上,但旋即又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扑下去捡……”
她的眼里又泛起汹涌的泪意,她颤抖着手想去抚平他的额头。这一抚,却令他真的舒展开来,唇里甚至溢出一声满足的喟叹。忽地,他的眉头又紧了起来,一定是梦,他又做这样的梦了吗?不!不要!他不要这样的美梦,梦醒时他的心会被摔在地上,碎成一地齑粉,鲜血淋漓,痛至百骸。
他的眼睛霍然睁开,在看到她的瞬间那眼里凌厉的烈焰却突然柔了下来,似挟了新鲜的阳光。
死生之间,恨意就淡了。那时他仰头看高墙倒下来,他什么都不想要,什么也要不起,意识模糊之际,脑子里只一个声音叫嚣,作践自己又有什么关系!权当他疯了!他就是要她!哪怕她恨透了他那又怎样?!只要能看着她,足矣!
他不敢开口,只静静瞧着她。
她穿了偏襟的团花旗袍,越发衬得肤如凝脂,鬓间有几缕碎发垂在耳际,当真是美不胜收。
她却不期红了一张芙面。
他心里突然一紧,如同久旱却降了一场绵长的大雨,她这样的情态,他何曾有幸见过?
印象中她很少对他笑,表情总是清冷,直冷到他骨子里去,而这样面红耳赤的样子他更是见所未见。
瑰丽的晚霞染透了晚天,郁秋娓娓道来。
林鹤唳听完却只是沉默,那样漆黑深沉的眸子没有丝毫外露的心绪。
郁秋心生了怯意,一方帕子被她在手里绞来绞去,脖子背心都闷出了涔涔的汗,褥衫浸了汗紧紧捆在身上,如同一件铁衣,箍得人窒息。
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久到郁秋心生了枝枝蔓蔓的绝望和颓败。她灰心地垂下头去,他那样不凡的人物,怎会是她郁秋召之即来的角色?她怎会这样高估自己?他曾经伤透了心,寒透了心,被她一刀刀割得满身鲜血,她不过是仗着他的喜欢,可现在,他不爱她了,她如何再有恃无恐地等他一句喜欢。
她吃力一笑,眼中泛起水汽,来不及了,她掩面,到底是来不及了。
“我想喝水。”低沉醇厚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
她怔住,表情惘然。
他又重复了一遍,“喝——水。”
她这才惊觉失神,忙拢了袖子去取茶杯。
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臂,林鹤唳拉得她脚下趔趄,差点栽在病床上,另一手却已经闪电般扯开她的袖口。
一只碧绿幽然的镯子静静躺在她皓白的腕子上。
郁秋赶紧收手,一抬头却撞进他含笑的眼里。
四目相对,千万冰山似乎在眼里塌陷、溶解,无需更多语言,只这一眼,已是心照不宣。
她赌气,“只不过是学着修玉器,好歹是门手艺。”表情却漏了笑意。
林鹤唳眼里分明是戏谑和促狭,“生了孩子我再教你骑马,英文和钢琴,样样都是手艺。”
郁秋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诧不已。
他哈哈大笑,“别以为我不在家,你的一切我都洞悉。”
羞愤几乎将她淹没,她脸上又是一红,“渴死你!”凌乱地抛下空杯子慌不择路地夺门而去,背后朗朗的笑声却追出她好远好远。
天边赤霞又潋滟了几分,或红或橙的色彩糅合在一起,旖旎成一片瑰丽绝景,林鹤唳忽地想起花园里次第绽开的花儿,芍药,杜鹃,海棠,连翘,金盏……那样的七彩斑斓不过是痴迷她时为她而栽,他征战杀伐,怎会沉溺这些莺莺燕燕?
她曾以为他流连百花,但她不知,姹紫嫣红皆开遍,他钟爱的,不过就那一珠百合而已。
信手拈来花几许,自此暗香甲中留。
因为独有她,才是他铠甲中那萦绕不去的疏影暗香。(原题:暗香)
推荐阅读 (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1爱情到了,请发货
2没有谁会讨厌直白热烈的女孩,我也不例外
3爱情就是,一个打死不说,一个口是心非
长按二维码下载【每天读点故事】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每天读点故事app」——你的随身精品故事库
如长按二维码无效,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