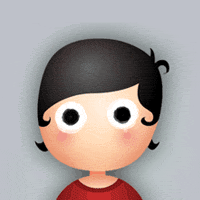70岁的张爱玲如何回望17岁的自己? 附《爱憎表》(选摘)
你最爱吃什么?叉烧炒饭
你的拿手好戏是什么?绘画
你最恨的是什么?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太早结婚
你最喜欢的人是谁?爱德华八世
你最怕什么?死!
张爱玲《爱憎表》
96年前的今天,一个女孩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人们从纷繁的书卷与逸闻中追寻她的足迹与心绪。21年前,她留给人世一个苍凉的背影。身虽去,坊间仍然流转着关于她的种种传说。她是张爱玲,一万人眼中有一万个张爱玲。那么,张爱玲的眼中的自己又是怎样的?
她如何看待生死?她少女时期学画画、学音乐有哪些趣事?最新发现的张爱玲“遗作”《爱憎表》,由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委托香港学者冯睎乾整理而成,不久之前发表于台湾《印刻》杂志。在她的诞辰,《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获授权全文刊载中文简体版,此为大陆首发。且看70岁的张爱玲如何回望17岁的自己。
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陈子善发掘出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37年校刊《凤藻》上中学毕业生张爱玲所写的调查表答案,并写成文章。张爱玲读到后,给宋以朗的父母、好友宋淇夫妇写信提到,“(调查表)隔了半世纪看来,十分突兀”,需要解释,于是花了约2个月写《爱憎表》,但陆续搁下。
冯睎乾在《<爱憎表>的写作、重构与意义手稿来历及相关文献回顾》一文中回忆说:“张爱玲的遗稿,可出版的,近年已悉数付梓,仅余小部分为未刊稿。2015年夏,宋以朗交给我一叠张爱玲的草稿,让我帮忙整理。当时草稿尚未诠次,仅按纸张大小、颜色和类型稍作分类,内容以作者往事为主,但很零碎。由于每页均字迹潦草,东涂西抹,宋以朗只能初步确定,手稿中包括一篇《爱憎表》散文,但原稿次序未明,也不知道页数。我根据草稿内容及其他线索,从中区分出26页纸,再排列次序,成功重构出部分的《爱憎表》。”
▲张爱玲遗作《爱憎表》手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在接受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遍览过张爱玲和同学交的35份调查表,其中,张爱玲的回答让他印象特别深,比如“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早结婚”“拿手好戏是:绘画。”相比其他同学对同样问题的直白答案,明显能看出张爱玲的早熟、多虑。“一般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考量生死命题,同龄中学生害怕的也多是父母责骂等家常事件,但17岁张爱玲早早开始思考终极问题了。”
《爱憎表》里还细述了张爱玲对绘画、音乐的看法,“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发现,从她与母亲关于艺术流派、古典音乐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张爱玲当年不仅有公认的文学才华,也有画画的才能。比如,散文集《流言》都是她画的插图,《传奇》《红楼梦魇》等作品的封面也是张爱玲自己设计的。”
▲左:张爱玲为《流言》画的封面;右:炎樱为《传奇》设计的封面
“岁数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80岁就会身价倍增”
在张爱玲看来,小时候人一见面总是问“几岁啦”,老了之后岁数又成为唯一的标签。她用略带调侃的口吻写道:但是这数目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80岁就会身价倍增。“一辈子的一点可怜的功绩已经在悠长的岁月中被遗忘,就也安于沦为一个数字,一个号码,像囚犯一样。在生命的两端,一个人就是他的岁数。”
少女时期的张爱玲家中有变故,父母关系让她压力很大,描写起带有分界线意味的17岁时,张爱玲笔下透露出同龄人鲜有的沧桑感——“我17岁,是我唯一没疑问的值得自矜的一个优点。一只反戴着的戒指,钻石朝里,没人看得见,可惜钻石是一小块冰,在慢慢地溶化。过了17就18,还能年年18岁?”她进一步解释,因为在“未知生,焉知死”的幼年曾经久久为它烦恼过,终于搞疲了。“所以我对于生老病死倒是比较看得淡。”
▲左:张爱玲自画像;右:张爱玲和李香兰合影
《爱憎表》里,张爱玲写到她与弟弟去北平公园附近新开的一家露天咖啡馆,花园里树荫下摆满了白桌布小圆桌。张爱玲点了一客冰淇淋,弟弟点了啤酒,“我诧异地笑了。他显然急于长大,我并不。也许原因之一是我这时候已经是有责任在身的人,因为立志学琴,需要长期锻练,想必也畏惧考验,所以依恋有保护性的茧壳。”
“母亲想培植我成为傅聪,但她不能像傅雷寸步不离督促”
回忆1937年中学毕业前在校刊上填“爱憎表”时,张爱玲开玩笑说,她还没写“我的天才梦”,“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也没人视为天才。不过因为小时候我母亲鼓励我画图投稿,虽然总是石沉大海,未经采用,仍有点自命不凡,彷彿不是神童也沾着点边。”
母亲劝少女张爱玲“选择音乐或是绘画作终身职业”。张爱玲起初不能决定,她姑姑也说:“学这些都要从小学起,像我们都太晚了。”当时,张爱玲母亲经常带回来许多精装画册,午餐后摊在饭桌上供女儿翻看。张爱玲喜欢印象派,不喜欢毕卡索的立体派。后来,当张爱玲决定学音乐时,半调侃半认真道:“(母亲)想培植我成为一个傅聪,不过她不能像傅雷一样寸步不离在旁督促,就靠反覆叮咛。”
▲张爱玲为她的英文原作《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配的时装图
后来,张爱玲跟白俄女琴师学钢琴,很贵,学了六七年,张爱玲写下如下一段:学校里教琴的老小姐脸色黄黄红红的浓抹白粉,活像一只打了霜的南瓜。她要弹琴手背平扁,白俄教师要手背圆凸,正相反。“又鼓起来了!”她略带点半嗔半笑,一掌打在我手背上。……我终于向我父亲与后母说:“我不学琴了。”他们在烟榻上也只微笑“唔”了一声,不露出喜色来。
对张爱玲来说,母亲与姑姑刚回国那两年,她们是童话里的“仙子教母”,给小孩带来幸福的命运作为礼物,但是行踪飘忽,随时要走的。“我姑姑弹钢琴我总站在旁边,彷彿听得出神,弹多久站多久。如此志诚,她们当然上了当。”小女孩“讨好”长辈的小“心机”展露无遗。
▲《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将全文刊载《爱憎表》中文简体版
《爱憎表》(选摘)
文:张爱玲
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往往啼笑皆非。最近的一篇是学校的年刊上的,附有毕业班诸生的爱憎表。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爱吃叉烧炒饭。隔了半世纪看来,十分突兀,末一项更完全陌生。都需要解释,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里又捡出这么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来。
最怕死
我母亲回国后,我跟我弟弟也是第一次“上桌吃饭”,以前都是饭菜放在椅子上,坐在小矮凳上在自己房里吃。她大概因为知道会少离多,总是利用午饭后这段时间跟我们谈话。
“你将来想做什么?”她问。
能画图,像她,还是弹钢琴,像我姑姑。
“姐姐想画画或是弹钢琴,你大了想做什么?”她问我弟弟。
他默然半晌,方低声道:“想开车。”
她笑了。“你想做汽车夫?”
他不作声。当然我知道他不过是想有一部汽车,自己会开。
“想开汽车还是开火车?”
他又沉默片刻,终于答道:“火车。”
“好,你想做火车司机。”她换了个话题。
女佣撤去碗筷,泡了一杯杯清茶来,又端上一大碗水果,堆得高高的,。我母亲和姑姑新近游玄武湖,在南京夫子庙买的仿宋大碗,紫红瓷上喷射着淡蓝夹白的大风暴前朝日的光芒。
她翻箱子找出来一套六角小碗用作洗手碗,外面五彩凸花,里面一色湖绿,装了水清澈可爱。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不喜欢吃水果,顿了顿方道:“香蕉。”
她笑了,摘下一只香蕉给我,喃喃地说了声:“香蕉不能算水果。像面包。”
替我弟弟削苹果,一面教我怎样削,又讲解营养学。此外第一要纠正我的小孩倚赖性。
“你反正什么都是何干——”叫女佣为某“干”某“干”,是干妈的简称,与湿的奶妈对立。“她要是死了呢?当然,她死了还有我。”她说到这里声音一低,又轻又快,几乎听不见,下句又如常,“我要是死了呢?人都要死的。”她看看饭桌上的一瓶花。“这花今天开着,明天就要谢了。人也说老就老,今天还在这里,明天知道怎样?”
家里没死过人,死对于我毫无意义,但是我可以感觉她怕老,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想保护她而无能为力。她继续用感伤的口吻说着人生朝露的话,我听得流下泪来。
“你看,姐姐哭了。”她总是叫我不要哭,“哭是弱者的行为,所以说女人是弱者,一来就哭。”但是这次她向我弟弟说,“姐姐哭不是因为吃不到苹果。”
我弟弟不作声,也不看我。我一尴尬倒收了泪。
我从小在名义上过继给伯父伯母,因为他们就只一个儿子,伯母想要个女儿。所以我叫他们爸爸姆妈,叫自己父母叔叔婶婶。后来为了我母亲与姑姑出国一事闹翻了——我伯父动员所有说得进话去的亲戚,源源不绝北上做说客,劝阻无效,也就不来往了,她们回来了也不到他们家去。我们还是去,但是过继的话也就不提了。不过我的称呼始终没改口。我喜欢叫叔叔婶婶,显得他们年青潇洒。我知道我弟弟羡慕我这样叫他们,不像他的“爸爸妈妈”难以出口。
有一天有客要来,我姑姑买了康乃馨插瓶搁在钢琴上。我听见我母亲笑着对她说:“幸亏小煐叫婶婶还好,要是小煃大叫一声‘妈’,那才——”
其实我弟弟没响响亮亮叫过一声“妈妈”,总是羞涩地嗫嚅一声。
关于倚赖性,我母亲的反复告诫由于一曝十寒,并没见效。七八年后我父亲还愤愤地说:“一天也离不了何干,还要到外面去!”
但是当时她那一席话却起了个副作用,使我想到死亡。那时候我们住白粉壁上镶乌木大方格的光顶洋房,我姑姑说“算是英国农舍式”。有个英国风的自由派后园,草地没修剪,正中一条红砖小径,小三角石块沿边,道旁种了些圆墩墩的矮树,也许有玫瑰,没看见开过花。每天黄昏我总是一个人仿照流行的《葡萄仙子》载歌载舞,沿着小径跳过去,时而伸手抚摸矮树,轻声唱着:
“一天又过去了。
离坟墓又近一天了。”
无腔无调,除了新文艺腔。虽是“强说愁”,却也有几分怅惘。父母离婚后,我们搬过两次家,却还是天津带来的那些家具。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无人。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份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象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迭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或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级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个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整个人生就是锻炼,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死后得进天堂与上帝同在,与亡故的亲人团聚,然后大家在一片大光明中弹竖琴合唱,赞美天主。不就是做礼拜吗?学校里每天上课前做半小时的礼拜,星期日三小时,还不够?这样的永生真是生不如死。
但是我快读完中学的时候已经深入人生,有点像上海人所谓“弄不落”了,没有瞻望死亡的余裕,对生命的胃口也稍杀。等到进了大学,炎樱就常引用一句谚语劝我:“Life has to be lived.”勉强可以译为“这辈子总要过的”,语意与她的声口却单薄惨淡,我本来好好的,听了也黯然良久。
但是毕业前一年准备出下年的校刊,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撇开死亡这问题。虽然已经不去妄想来世了,如果今生这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斩断剥夺,也太不甘心。我填表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甘冒贪生怕死的大不韪,填上“最怕死”。
(《收获》杂志授权)
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制作:姜方
·END·
往期热文
文艺精华 如您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