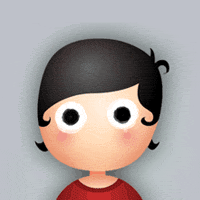虫痴和蟋蟀
中秋一过,蟋蟀争雄之时,每每就會想起了蟲癡。蟲癡是个虫迷,又是个辨虫养虫的好手,每当秋风乍起,就是他最忙的时节了。跑山东,下河北,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他会舍得花一头牛犊的价格去买一条小虫;早秋不菲的成本,使他成了搏奕场上的常赢家。
蟋蟀好斗,人好赌,蟲癡有着粗犷的性格,话说得也很坦然:“我养虫不是什么陶情养性,就是为了赢钱”。每次从场子里得胜回来,他就会邀几个朋友小聚;谈起虫经来,他真是喜形于色,乐不可支。有次在席间,我跟他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带我进场子,让我见识见识。蟲癡沉吟了一下,答应了。
后来我才知道,进场的人数是受限的,我挤占了他虫友的一个名额。三年前。深秋,中午。广中路中山北路口。进场子是由专车接送的。我,蟲癡和他的虫友Y等着,聊着。他俩都背着个相同的皮包。Y长得胖胖的,一身运动服。看模样,象个跑龙套的。在聊天中,我也知道了些大概。
原来斗虫就象走程序一般变得复杂刻板;分三天供养,五天供养,七天供养。在同一环境下,饮食相同,杜绝了某些虫主给虫子使用兴奋剂的可能性。三天,五天是些小场子,人是能随便进出的,安全系数也小些;七天就不同了,它是纯商业化的运作;有着配套的一条龙服务,简易的吃喝不收分文。隐蔽性很强,虫主事先都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抽头也高达十个点。
当然,场主也非等闲之辈,他雇用了一批专业人员,被爆的概率很小。用蟲癡的观点:这种场子是不会出事的。一辆大巴在路边停了下来。开门,司机是位五十开外的秃顶,蟲癡和司机认识。由于蟲癡长得高大,他只得低头弯腰,我们朝车厢后部走去。“毛胡子,你和朋友把手机都关了。”我们的身后传来了有些沙哑的声音。
其实,在这之前蟲癡已吩咐过了。这防范措施倒是很到位的,局外人很难入这种圈子。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神色都很淡定,其中竟有三个女的,岁数也就三十开外吧。她们在和旁人轻松地说笑着,好象是外出去旅似的。我有些纳闷了,这种玩心跳的游戏,女人也喜欢?
大巴从中山北路上了高架,不久开上了沪青平公路,进入了平望镇,在一农家大院前慢慢地停了下来。车上三十几人依次下了车。临下车,蟲癡丢给了司机一支烟,说了声:“你辛苦了!”秃顶狡黠地笑笑,哑着嗓子:“混口饭吃呗。你好运啊!”说完了客套,就关上了车门。
然后,我们随着人流进了这显得有些僻静的农舍。这是幢洋房样式的三层楼建筑,落成时间不长。进院,才发现里面是另一番天地,花园很大,绿绿的绒般的草坪上,裁着十几株长得很茂盛的黄杨。一条宽度近五米的鹅卵石铺成的甬道直通楼房。底楼共有六间房,正处在装修停工阶段。每间屋放着一些排档上常见的塑质桌椅,角落里堆着几箱三得利乌龙茶。一些人正闲散地坐着,喝着茶,聊着天,声音都很轻,人虽然很多,但一点也不显得噪杂。我原以为这种是非之地,一定是乱哄哄的,想不到竟这么有条不紊。
一个青年走了过来,跟蟲癡耳语了几句,就急急地走开了。蟲癡拿出了包中的一个塑料小牌,递给了Y,轻声慢语:“你,上二楼吧。”Y走后,蟲癡跟我说:“开场前,蟋蟀得先秤体重,过去是毫戥秤,俗称‘横’,现在是专用的电子秤,快又方便,上下二点,就可配对了。”蟲癡又拿出了烟:“来,再抽一支,上面是不能吸烟的。”我隐约地感到蟲癡点烟的手似乎有些抖。我知道,来这里聚赌的,可都是些市、区级的模子。
这场子入册一万,也就是说,最小的赌注从一万始。没过多少时间,Y就领我们上了二楼,进入了一间已经有很多人站着的房间。这间斗房,大约有三十来个平米,中间放着一张略显长方形的桌子,旁边围着几圈人。桌的正中摆着一个圆形的转盘,上面椭圆形的有机玻璃斗格下垫着一沓白白的草纸。对手分站在桌子两旁,中间站着监板(裁判),他的下手各立着两位年轻人,桌子的二边各放着一台点钞机。
监板是个年近七十的老头,瘦瘦的,带着付黑宽边眼镜,看上去就象个绍兴师爷,他的声音清晰威严:“入虫!”二只蟋蟀由过笼进了斗格。“三斟七,正码(体重相同),摆花(下赌注)!”师爷的声音很响。一口上海方言夹着普通话。蟲癡看了看对方的虫子,应道:“打台花(入册数)。”对方没有应答,嫌少了。看对方三人的衣着打扮,就象个工人阶级。蟲癡的这条虫是紫壳白牙,也算是蟋蟀中的上品。对方是条黄督,乌头黑脸,一副凶相。与此虫相遇,凶多吉少。蟲癡真是熟谙此道,其实,他真实的想法是想避开这条虫。
“苍蝇,苍蝇,帮帮花!”师爷扫视了一下桌子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撑五只!”一个尖细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是个女的。桌前有人让出了空档,一个女人挤了进来,是和我们同车的其中一位。原来她是来飞苍蝇的,一只苍蝇价五百。很快,苍蝇加到了三十只,就在也没应声了。“好了,呒要在逼花了。”监板的话说得很委婉:“行了么?要么撒虫?”老头与对方商量。工人答应了。两个年轻人的点钞机开始工作,液晶屏上显示的数目是250。
“开局!”师爷的话讲得规范简单:“起草!”双方的虫主开始用芡草引逗蟋蟀,以其起兴。蟲癡的草功明显比对方略胜一筹,只见他手腕轻抖,一杆草在小虫身上上下翻飞,白牙虫性大发,围着草杆嘶咬,鼓翅而鸣。瞧那督銮也是张牙提翅,八角有风。“起闸。”
话音刚落,监板已掀开了斗格的栅板。又是一句话:“领正,”虫主用草点定蟋蟀,不让其任意走动,双方引虫正面相迎,“交口!”说时迟,那时快,铮铮几口,口口有声,两条虫已纠缠在一起了,造桥夹,结球夹,好一场恶战,众人发出了唏嘘声。待二虫分开,紫壳白牙已少了一条大腿,一蹶一拐,落荒而逃。它的身后,草纸上沾着点点血水。
在看那黄督,抱头爪也被咬断了,但它还在两须横扫,振翅长鸣。蟲癡没吱声,转盘一转,很快提了虫,这也许是他意料中的。斗格下的草纸拿去了几张,第二局又开始了。对手换了人,象群做生意的,其中一个矮胖子,脖子上围着鼓鼓的金项链,两手腕上都套着粗粗的金手链。虫儿入格,一条白披顺势依在格边一动不动,白斗丝,黄脑盖,看起来文绉绉的。
对方是条红牙青,黑头黑脸,虎虎生威,在草纸上来回不停地走着,沙沙有声。蟲癡正眼也没瞧对方的虫一下,只是目不转晴地看着自己的虫,胖子以为他还没从败局中回过神来,干笑了二声:“呵,阿拉是要花额,侬先钦。”“十只!”蟲癡抬头,双眼紧盯对方,斩钉截铁地说道。商人怔了一下。苍蝇都朝蟲癡这边飞了过来,一下过了十九万。“停,好啦。”商人很急地说。大话出口,覆水难收。
在这场子里,有钱人多得是。更何况毛胡子在虫圈中有些小名气。师爷发话了:“并并拢,凑足廿只吧。”“好,好。”商人一迭声地说,可声音小了半截。点钞机工作了几分钟。商人被烟熏得蜡黄的手指下草时有些抖,那根草逗得红牙青追腾扑咬,乌黑金翅,鸣声洪亮。
蟲癡手中的芡草轻点了白披的尾端,不动的虫子猛地转过身来,张翅无声。
起闸后,白披龙行虎步循声而走,虫须相逢,四牙交错;似闪电,只一口,已见红牙青须根破裂,两牙不能启合;在斗格中急急地乱窜,笼形也没了。而白披在草格正中,两须扫地,摇头探脑,还在寻着对手,似乎没尽兴。众人啧啧称羡。“好虫!介结棍,这么重的口,少见,真是虫王级别。”监板赞道。商人连虫也没提,就离开了。
两个年轻人为下注的苍蝇发赌金,这么多人,竟没一个搞错的。许多人围上了蟲癡,蟲癡很大方地说:“走,下面抽烟去!”……这一天,蟲癡斗了五条虫,三胜二负,赢了不少钱。
蟲癡走了。这条线断了。以后我就再也没进过场子。
文:匆匆過客//編輯:小馬哥
每日更新蟋蟀打斗视频,蟋蟀趣闻,蟋蟀捕选养斗秘笈,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