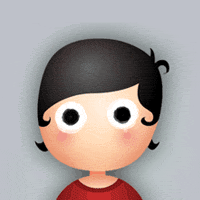荐诗|简的诗
简的诗
简
前言
﹀
﹀
﹀
彭逸林教授在谈到张枣作品时认为张“有优雅的控制力”,我深以为然。正是这种控制力,让张的诗令人心醉神迷。控制力,就是游刃有余,抑或就是从容。这也是一个诗人趋于成熟的表现。除了一些实验性的文本,控制力是诗歌的守则之一。即便是实验文本,也是讲究合适的度。
简的诗歌,内敛收缩,呈现人的普通情绪,但是往往能找到弹性所在,将诗意的张力扩充到一定程度,而又引而不发,仅留下路标,不说满,不写满,不把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复述一遍来浪费语言,而是让读者既能感受到痛感,而又不撕裂,这是隐痛,而隐痛往往令人更痛。
《星星》在推出简的作品的时候,进行了有趣的探讨。其中《两个母亲的对视》,这两个母亲分别指的谁?我想这正是这首诗成功之处,不直接说出,而是暗示。假设直接说出一个母亲是狗,一个母亲是“我”的时候,诗歌的意味便会荡然无存。
这就是简的诗歌控制力所在。不过,这不是优雅的控制力,而是紧促的控制力。越控制,越紧张,越紧张,越欲罢不能。诗歌的言外之意,留白或者空间,就会更大,路标指向的纵深就会越宽泛,并能更大程度激发读者的想象力。
所以,我一点不奇怪《星星》将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的简,放在头栏头条。难得的是,简将82首作品投到《诗刊》的公众邮箱,竟然被张二棍发掘,组诗发在《诗刊》银河栏目。
诗歌
﹀
﹀
两个母亲的对视
我羡慕她高大肥壮的身子
她用牙细咬腋下发痒的部分
她望了我一眼,走向主人的灶台
我们在同一个时段打瞌睡
我们在同一个时段想孩子
她用浑黄的眼睛凝视我,摇尾巴
也许嗅到我腿脚的善良
看见她干瘪下垂的
我忍不住摸了摸我毒素淤积的地方
我听见骨骼的脆响
不知何时,我的生活开始疼痛
总是这样重复
弯下腰抹掉饭桌上的油迹
弯下腰,拖干净地板上的污渍
弯下腰,拾起零落的发丝
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弯下腰
每次要站立起来
我总能听到腰部骨骼的脆响
为了不触碰那根骨头
我开始练习,挺直背脊
守水
香炉村的炎夏,水是有秩序的
从庄子坝修过来的水渠
像漏时间一样漏水
想要接住漏下的水
必须为自己的稻田打开一个缺口
父亲像鸟雀守着林子一样
守到月落西山,晨星渐起
便有水可引入稻田
有时,守着守着父亲在岩洞下睡着了
前面稻田里溢出的水
经过他的鼾声,又流到下一个稻田了
送五味子的妇人
她苗条地闪过灯光下
递来一小袋五味子
宝宝的母亲努力挤出微笑
接过袋子
她明知那天妇人在田里扯草
宝宝爸在楼下劈柴
砍一斧头,向田里望一下
砍一斧头,向田里望一下
她仍然接过五味子
她明知宝宝妈
知道她被宝宝爸多望了几下
她仍然送过五味子
宝宝正一口一口
那么多种味道被他吃成了
奶一样
电线割伤手心
三叔的坟墓才砌好
小艾奶奶从儿子的坟墓回来
腿脚发软
一把抓住板壁上的电线
像抓住三叔似断未断的呼吸
小艾奶奶不断抽搐
电流收走她所有的爱
三叔的呼吸收走她所有的爱
伤口在她手心长了好多年
孙儿都上大一了
摸摸手心,依旧疼得裂肺
扫玉米
秋风过后,她的头发又白了一些
水泥地上的玉米粒也白了一些
她拿扫帚想扫出一条路
每一次弯下身子,就扬起一阵灰尘
她怕灰尘沾染了我
她的灰尘飘过她的一生
飘过经幡一样的农家彩旗
她开始扫第二遍
玉米粒越聚越拢
扫帚越来越重
她站在灰尘中,又老了一点
伍婆走了
她应是笑着走的
她地里的玉米也笑着
丝瓜开满了花
她太瘦了
揣不走人间的疾病
她用惨白的脸
收走了多年的腊黄
她放下背篓,放下锄头
放下一生的佝偻
终于挺直了腰杆
和腿脚
龟石
它守着一座长满蒿草的旧房子
用了多长时间,它才将肉身坐成了龟甲
我很喜欢它低头的跪姿
也许等得太久了
它伸出一只前足立在地上
探向落日的方向
夕光一样沐浴着它
我已深深着迷,这决心赴水的石头
蓬勃
村里的野草太青了
人们一到外省去,它们就长进家里
屋顶都是
人们不种玉米了,它们就长进地里
路上都是
人们不再砍柴了,它们就长进山里
新砌的坟头上都是
长势太好了
就快长进城里了
石头硌疼的
月亮岩下的路有着月亮匐岩的耐心
路上的碎石,一不小心就硌着谁了
曾经,它硌伤过上山的羊群
硌疼过开县过来的生意人
硌翻过打货的大卡车
一条路能忍心硌疼人间多少事物?
它止不住雪宝山的熟地迅疾成林
止不住两旁越长越拢的草
今天,唯一一个种木香的人
双手和膝盖,被硌出了血
当一会儿他的妈妈
他站在水缸旁玩儿水
他换下玩湿的厚衣服
他说不出爷爷去哪儿了
他挨着我坐在一根松木上
他甚至小心地把头靠在我身上
就当一会儿他的妈妈
仿佛他外公不曾踢过他
仿佛他忘记了今天只吃过一顿饭
那个六月里穿夹袄的小男孩
那个五岁了
还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的小男孩
青冈树
香炉村的悬崖有各种长相
水凹口下的巨花崖一匹站在一匹肩上
崖肩的一排青冈树,以跳崖的姿势
为经过的羊群让路
那年幺舅去崖顶砍柴
他站在崖的对立面,拉紧捆柴的绳子
绳子有时以结的方式,结束一个生命
有时以断裂的方式
青冈树只轻轻伸开手臂
就挽住了一个坠向深渊的人
向日葵芽
它动用所有感官从黑暗中摸索光
它动用所有力气从泥土中抬起头来
两枚浅绿的芽叶双手合十
继而探向不同方向的露珠、阳光
几乎所有事物一开始都是这样
渐渐长大,渐渐世间有了应有的模样
一部分开出了花,挂了果
另一部分,则小心翼翼,学会了生活的尴尬
挖土豆
土豆通常与玉米杂居
共享牛筋草、念根藤、鹅肠菜
也共享蚯蚓和蚂蚁
母亲一生都在挖土豆
开始在山上挖,后来在田里挖
母亲每挖出一窝土豆
就得先折下不断向她刺来的玉米叶
汗湿的头发和草屑一起贴在她额前
她下的每一锄都无比小心
就像从子宫里掏出儿女
看病
简,收据拿来
伸左手
母亲坐在采血窗口前
无名指的血液在微量吸管里
一点一点爬高
简,随我进来
母亲跟着女医生走进放射室
“正在放射”几个字越合越拢
直到母亲从门缝里消失
医生每一次喊到我的名字
母亲就乖乖地替我扎针、喊疼
替我吞下一枚枚药片
她所有忘记的
那张以我命名的小小磁卡
一一替我记着
管辖
我只管做作业,弟弟只管玩儿
父亲只管去东莞或潼关
母亲权利太大了
五个人的土地、稻田和山林,要管
年猪、鸡群、耕牛,要管
唯一管不了
奶奶越来越不认识我们了
我胆囊长息肉,医生都配了肾炎的药
母亲的胃,在一天天陷入糜烂,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自由
母亲太自由了
太阳未出山时,她去红薯地收露水
太阳当空时,她在玉米林里释放汗水
如果饿了,喝口酒又可以下地
群鸟归巢后,有一地银霜陪她回家
一个人踞守的庄稼地
她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多年以后,糜烂的胃,腿部的风湿
突出的腰椎
才有一搭没一搭地责怪她
患尿毒症的女孩
我路过一段音乐的忧伤
它来自一张有字的布,摆有四川某大学的学生证
和西南医院的B超单
它来自一个双膝跪地的哥哥
捧着钱不断道谢的哥哥
它来自一张简便的椅子
椅上躺着的女孩
始终紧闭双眼
红色薄毯,让这个世间稍许温暖
蓝色口罩,让这个世间说不出话来
和母亲谈死亡
用手指摩挲着皱纹
母亲说,她这棵树水份正在流失
叶子已泛黄,开始脱落了
我想到山上那么多的树
在使劲长
她说,脖子上的那根筋
连到下巴时,人就要走了
她又捏了捏松软的脖子
我提到老家消失的松树、杨树
母亲笑说,她已赚了十几年
我还是不敢盯着她的脖子看
叩门人
像那棵栾树躺在大地上
我们从根出发
事先就定好了枝丫的走向
每一处分枝,都会走掉一些人
叩门声,如栾果丁当
要么,高于人的苦蒿封锁了门
要么,笑而迎你的
尽是白发多病的手杖
月亮照着的
稻田到家的距离
有时是一场争吵
我们在院坝里首先看到了父亲
然后是大段的黑夜
焦虑缩成一团云
月光最长情
照着母亲回来
又照着母亲下山
黑夜究竟有多黑
一袋稻谷扔下多少黑
母亲从未告诉我们
她只慢慢地,从一段黑
走到另一段黑
午餐
人们陆续入坐
他的两个女儿为客人一一盛上饭
他的老婆为客人倒上米酒
客人们迟迟不动筷子
他的筷子摆放得整整齐齐
他的杯子盛了小半杯酒
他的座位一直空着
他离世的第六天,村子忍不住大雨
下雨
他的车子撞上隧道墙时,在下雨
人们把他拖出残渣样的司机室时,在下雨
他不让身体有一处冒血
躺在棺木里时,在下雨
他的两个读书的孩子赶回家时,在下雨
我们驱车前往他的墓地时,在下雨
我们在田里烧他的衣服时,在下雨
他的母亲和姐姐抓着他的墓碑哭泣时
雨下得更猛烈了
他坟头的碗,已盛不住雨水
汽车临行前
以为是检票员
她像从天而降,递过来一个小本子
纸上写着:
姓罗,10元
姓王,10元
姓肖,5元
……
那页纸收回去又伸过来
多了一张明信片,手指指着
“一级聋哑”
递给她十元钱
我对仿佛长在我面前的本子,摇着头
猝不及防的,她为我戴上一只红色手链
转动着手链上的木珠子
仿佛我拥有了她悄无声息的一生
两只????子
也许是夫妻,也许是兄妹
他们警惕地活着
圈养的铁笼挂在河堤树丛边
他们无心接受逝水的叹息
要提防,一波一波前来的窥视
不断地抓跳,过笼风仿佛永不安宁
他们偶尔迅捷地抢过人们手中的一根草
像抢过一次嘲讽、挑逗
或试探。他们仿佛还在练习
逃过捕兽夹的牙齿
他们咬断草茎的咔嚓之声
太像遗失右脚的一瞬
洗衣石
靠着兴隆坝的一面墙
几匹砖支撑着它二十多厘米厚的身子
盆子里的衣服用时光打磨
它越来越薄,越来越接近水的模样
它的命名像兴隆坝的人一样
开始模糊
我忍不住抚摸了它正中心的几个字
——李公勝德老大人
谈论
谈到对岸那座山
我们都如坐春风
谈到山上的树
仿佛我们都变绿了
谈到山上应该有条乡村路
两位叔叔都急了
他们无法安置那么多树木
谈到可以一个骨碌就回去了
我突然很失落
回到故土的过程,应该像蚂蚁一样
一点一点,慢慢爬
老柳
他从未想到高过那幢教学楼的楼顶
甚至好多年前就不再向顶端输送水分
他着迷于已有的垂条,像瀑布一样悬挂
粗糙的皱纹里,青苔渐枯
他终生致力于接近地面
没有一个小孩反对他的接近
所有小孩,包括我,都在学习他
从地面长起来,又回到地面去